文| 洛伊 纽约时间
据纽约时报报道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美国最著名的公共卫生家安东尼·福奇即将退休,他在《纽约时报》撰文,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讨论哪些意外推动了他的事业。

尽管我不愿使用“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这句陈词滥调,但当我准备离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50多年后的工作时,确实有这种感觉。当我回顾我的职业生涯时,我看到了一些对下一代科学家和卫生工作者或许有用的经验教训。
在81岁的年纪,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开车来到位于贝塞斯达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田园般的园区时的情景。1968年6月,当时27岁的我刚在纽约市完成住院医师培训。当时我最渴望的是成为我所能做到的技术最高超的医生,致力于为我的病人提供尽可能最好的护理。这仍然是我的身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我没有意识到意想不到的情况会对我的事业和生活的方向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我很快就学会了迎接意外。
我分享我的故事,一个热爱科学和发现的故事,希望激励下一代进入与健康相关的职业,并坚持到底,不管一路上可能遇到何种挑战和意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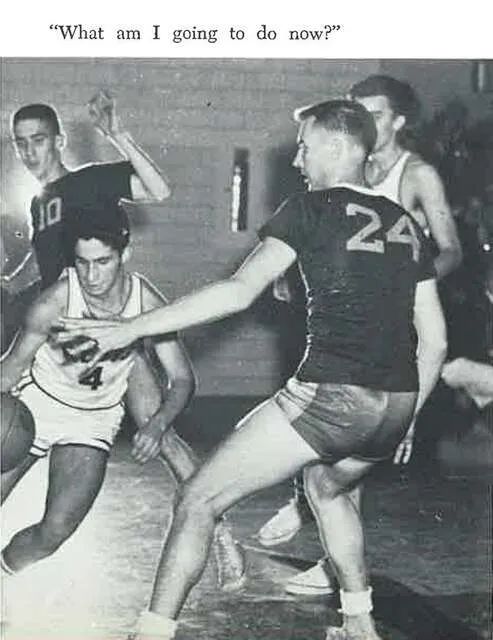
正是在我的住院医师培训期间,我开始对传染病与相对新生但蓬勃发展的人体免疫学之间的联系着迷。我照顾了许多患有感染的病人,有的病情很常见,有的却是疑难杂症,我清楚地认识到,医生和其他医疗保健提供者需要更多的工具来诊断、预防和治疗疾病。
为了将这些兴趣融合在一起,我接受了NIH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的一项研究工作,学习细胞和免疫系统的其他组成部分如何以复杂的方式保护我们免受传染病的侵袭。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需要遵循国家卫生研究院从实验室到临床研究的传统,将实验室的发现转化为对病人的护理,反过来也要将临床的见解带回实验室,以改进科学。
尽管之前没有接受过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训练,但我却意外地被它所蕴含的潜在发现所吸引,这些发现不仅会使我的病人受益,还会使无数我可能永远不会遇到的人受益。我对这项工作的新爱好与我精心制定的行医计划产生了重大冲突。最终,我选择同时追寻这两条路:成为一名研究科学家和一名在NIH治疗病人的医生,从那以后我一直在那里工作。
在实验室和诊所里可以有如此多的发现——即使是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为一组被称为“血管炎综合征”的致命血管疾病开发高效的治疗方法。原本可能会死亡的病人,却因为我开发的治疗方案而获得了长期的缓解。我可预见的未来似乎已经勾画好了蓝图:我将终生致力于与异常免疫系统活动相关的疾病研究。
然后,在1981年夏天,医生和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神秘的疾病,主要在男男性行为的年轻男性中传播。我开始对这种不同寻常的疾病着迷,这种疾病后来被称为HIV/AIDS。它的标志是人体抵御它所需要的免疫系统细胞遭到破坏或损伤。我也对那些男同性恋者产生了强烈的同情,他们已经被污名化,而现在病情加倍地折磨着他们的身体,偷走他们的生命和梦想。

我决定彻底改变我的研究方向,而这令我的朋友和导师们大为沮丧的是——他们认为我这样做会使蒸蒸日上的事业戛然而止。但我终究没有听从他们的劝告。此后,我将全身心投入到艾滋病研究中,在国立卫生研究院医院里医治这些年轻人,同时在实验室里探索和揭示这种新疾病的奥秘——到如今,我从事这项工作已经有40多个年头。
我是亲力亲为的医生,也是临床研究员,我很享受自己的身份,也从未渴望担任重要的行政职位,但是,20世纪80年代初,对HIV/AIDS的研究相对缺乏关注和资源,这让我感到挫败。一次意想不到的机会再次出现,我被邀请领导NIAID,我接受了这个邀请,条件是我需要继续照顾病人,并领导我的研究实验室。这一决定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并为我提供了以我从未想象过的方式积极影响医学和全球健康的机会。
从罗纳德·里根总统开始,在我38年任职NIAID所长的职业生涯中,我有机会亲自为七位总统提供建议。我们讨论的议题包括如何应对HIV /AIDS,以及其他威胁,如禽流感、炭疽热袭击、2009年大流行性流感、埃博拉、寨卡和新冠。我总是对总统和其他高级政府官员说出不加修饰的真相,即使这样的真相可能令人不舒服或在政治上不讨巧,因为当科学和政治携手合作时,会发生非凡的事情。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拯救生命的HIV抗病毒药物被证明是安全有效的,而这些研究多数是获得了NIAID的支持。1996年,这些药物在美国上市。到21世纪初,能够获得这些药物的人可以预期几乎正常的寿命。但是,对于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其他中低收入地区的人们来说,几乎不存在获得药物的机会。
在乔治·W·布什总统深切的同情和对全球卫生公平的渴望的驱使下,他指示我和他的工作人员制定一个项目,为资源贫乏、HIV感染程度高的国家的人们提供这些药物和其他护理。能够成为“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的设计师,是我一生的荣幸和荣耀,该计划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挽救了2000万人的生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是一个例子,说明了当政策制定者立志实现以科学为基础的大胆目标时,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如果我在国家卫生研究院职业生涯的远端是HIV/AIDS,那么近端是新冠。这次大流行并非完全出乎意料,因为新出现的传染病在历史上一直挑战着人类,但有些疾病可以改变文明,而新冠是自1918年流感大流行以来影响人类的最具破坏性的呼吸道疾病大流行。而且,对于新冠的持续经验,我们可以从它中学到很多东西。

它提醒美国注意继续投资基础和临床生物医学研究的重要性。新冠大流行的重大成功是由科学进步推动的,特别是已研制出的挽救生命的疫苗,这些疫苗在临床试验中被证明安全有效,并在一年内向公众提供——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壮举。
其他教训是痛苦的,例如美国国内和全球某些公共卫生应对措施的失败。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对抗新冠的斗争受到了我们社会中深刻的政治分歧的阻碍。有关佩戴口罩和接种高效安全疫苗等公共卫生措施的决定,竟然会受到虚假信息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一点是我们前所未见的。
确保公共卫生政策决策以现有最佳数据为依据,是我们的集体责任。科学家和卫生工作者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大声疾呼,包括向新的和传统的媒体发声,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分享和解释最新的科学发现以及尚待了解的知识。
当我回想起1968年来到NIH的那位27岁的年轻人时,我为我通过向美国和全球公众服务而获得的荣誉而深感谦卑。
在我的实验室、NIH诊所、NIAID研究部门,通过国内和国际研究合作,我结识了数以千计出色而敬业的医生、科学家和支持人员,我与他们亦师亦友,在教学相长中,我体验到了巨大的喜悦,受益无穷。
展望未来,我相信,下一代年轻医生、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在满足保护、修复和呵护世界各地人民健康的专业知识的巨大需求时,将体验到与我同样的兴奋和成就感,勇敢迎接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挑战。
(声明:本文为《纽约时间》授权转载内容,版权归《纽约时间》所有,未经授权和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任何形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