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报道,德国科技公司Wirecard受到德国上层精英人士的欢迎,被认为是德国在金融技术和数字时代的代表企业。但在其高企的股价和创新业务的外表下,满是谎言、犯罪和阴谋,其COO还和与俄罗斯情报部门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揭露这一切的,是金融时报的一名记者和一名编辑。

2020年春末,奥地利银行高管扬·马萨利克被停职。
他在欧洲商界名望甚高:极具感召力,会说三国语言,而且办事游刃有余。
在他最繁忙的时候,即作为德国发展最快的金融巨头Wirecard的首席运营官时,他也会向那些想占用他一些时间的下属保证,他总会为他们预留时间。
他常说:“为了你,我永远都有时间”。但他基本对每个人都这么说。
马萨利克的身份与公司的身份密不可分,这家公司是一家总部设在慕尼黑城外一个小镇上,拥有银行从业认证执照的全球支付处理商。他在2000年的20岁生日加入时,公司还是一家初创公司。他没有科班出身的资历或业内工作经验,但他对Wirecard的发展表现出不遗余力的奉献精神。
公司最终赢得了德国政界和金融精英的信任,他们认为Wirecard是贝宝在欧洲的有力竞争对手。当Wirecard想要收购一家中国公司时(注:银信支付),前德国总理默克尔亲自向习近平提出了这个建议。
然后,在2020年6月18日,Wirecard公司宣布,公司账户中丢失了近20亿欧元。这笔钱相当于Wirecard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所报告的全部利润。只有两种可能:钱被偷了,或者钱根本就不存在。
Wirecard董事会让马萨利克暂时休假。据说失踪的资金被存放在菲律宾的两家银行里,而Wirecard的亚洲业务属于马萨利克的管辖范围。当天离开办公室前,他告诉大家他要去马尼拉找到这笔钱。
当天晚上,马萨利克在慕尼黑与朋友马丁·魏斯见面吃比萨。魏斯一直担任奥地利情报机构的行动负责人,直到最近。现在,他在政治、金融和犯罪的交界贩卖信息。
魏斯给一位极右翼前奥地利议员打电话,让他为马萨利克安排一架私人飞机,从维也纳附近的一个小机场起飞。第二天,据称另一名前奥地利情报官员,开车带着马萨利克向东行驶了约250英里。马萨利克只携带了手提行李,向飞行员支付了近8000欧元的现金,并拒绝接受收据。
菲律宾的移民记录显示,马萨利克在四天后,即当地时间6月23日入境。但是,就像关于Wirecard的大部分业务一样,这些记录都是伪造的。虽然奥地利人一般不允许拥有双重国籍,但马萨利克至少持有8本护照,包括加勒比海小国格林纳达的外交掩护。他离开的奥地利巴特弗斯劳城镇,是已知他使用真名的最后一个地方。
——————–
Wirecard的崛起并不是凭空实现的。相反,它融合了各种因素,正如对冲基金经理吉姆·查诺斯(Jim Chanos,著名卖空者)所说,这些因素使过去五年成为“欺诈的黄金时代”。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试图重振低迷的经济,中央银行压低利率,使企业获得贷款的成本降低。风险投资和科技界充斥着宽松的资金,形成了一种贩卖故事和雾件(注:过早宣传不一定能真实发售的产品)的文化,其中充斥着高高在上和异想天开的想法,而缺乏的是实际明确的实施路径。
Reddit论坛网友号召股票散户抬高GameStop的股价,冲击华尔街的投资大行,起义代号为YOLO(及时行乐)。离岸加密货币交易所发布了自己的代币,作为数十亿美元贷款的质押品。
2021年底,在投资热潮中,《股票魔法师: 纵横天下股市的奥秘》和《股票魔法师2:像冠军一样思考和交易》等书的作者马克·米内尔维尼成为CNBC嘉宾,每月向人们收取1000美元,购买他的私人市场研究报告。
他还推荐过一家名为Upstart的科技公司,声称其收益“非常强劲”、“名字好听”。
节目主持人问他:“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
“呃,你说什么?”
“Upstart是做什么的?”
“呃,嗯……我,我……我很抱歉。”
“这是到底个什么样的公司呢?”
这位嘉宾说:”对,我不太……我没听清你的话。”(Upstart的股价此后下跌了95%)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德国机构选择支持Wirecard。德国的传统产业是汽车和能源系统,包括宝马、大众、戴姆勒、西门子等。Wirecard代表德国发起对硅谷的挑战,标志着公司向金融技术和数字时代的飞跃。
德国议员弗洛瑞安·唐卡指出:“德国的政治家们很自豪,终于可以对外宣称‘我们也有金融技术公司了!’”
Wirecard的股价上涨表明企业是可靠的,其批评者是无知或腐败的。德国《商报》称,Wirecard的首席执行官是一个“大师“,他“如圣灵一般穿越德国金融界”。最终使这家公司倒闭的不是监管者或审计师,而是伦敦的一名记者和他的编辑。
——————–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丹·麦克鲁姆经常开玩笑说,他的婚姻是一个小型骗局。他与妻子相识的时候还是一个银行家,但最后自己成为了记者。
当他20多岁时,他已经在伦敦的花旗集团工作了4年。他说这段时间足够他身处业内进行观察和思考。他对我说:“那里没有我想要的东西。”
一天晚上,他和一群同事出去吃饭,他说:“大家都在抱怨自己的工作。”一位年轻女士建议他们围着桌子,分享自己的真实愿望,其中大部分需要通过多年培训或高级学位才能实现。
他说:”到我时,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想成为一名记者’,而提议的那位女士只是看着我,好像觉得我有点傻,她说‘好吧,那你就去做吧’。”
这次的时机是偶然的。18个月后,2008年7月,作为《金融时报》的一名菜鸟记者,麦克鲁姆被派往纽约,在那里他目睹了雷曼兄弟的倒闭和随之而来的混乱。
到那一年年底,麦道夫的庞氏骗局已经解体,让投资者损失了大约65亿美元。麦克鲁姆回忆说:“我们仿佛找到了放大镜,如果如此严重的欺诈行为可以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那么所有东西都可以造假。”
2014年夏天,麦克鲁姆在伦敦寻找报道灵感,有一位对冲基金经理问他:“你对德国黑帮感兴趣吗?不过一定要小心行事。”
2000年,在Wirecard成立一年后,公司几乎崩盘,部分原因是它聘请了马萨利克来负责公司向移动时代的过渡。
麦克鲁姆在2022年出版的一本名为《金融家:一个热门创业公司,一个十亿美元的骗局,一场为真相而战的斗争》(Money Men: A Hot Startup, A Billion Dollar Fraud, A Fight for the Truth)的书中写道:“第一个警告信号是,公司系统的崩溃后,Wirecard的工程师将问题追溯到了马萨利克的办公桌上。”

“在一次‘意外事件’中,他将公司互联网流量全部导向自己的私人电脑,而不是经过服务器的专用硬件,这种设置非常适合窥探情报。”
但是,作为一个有天赋的黑客,马萨利克不能被解雇。他的工作是从零重建公司用来处理支付的软件。麦克鲁姆说:“这个项目太重要了,而且进展太快,不能让新人重头再来。”
大约在同一时间,名叫保罗·施利希特格尔的德国商人,尝试进军在线支付领域,重点是色情制品领域。当时并不缺乏需求,但那是拨号互联网时代的终点,施利希特格尔提供的支付系统也很笨重。
当他得知Wirecard可以处理信用卡和借记卡交易时,他提出要收购这家公司,但被Wirecard拒绝了。实际上,公司当时已经身陷困境,在其办公室被盗后,公司濒临破产。施利希特格尔以50万欧元的价格买下了公司的剩余股份。
在2000年早期,Wirecard的公司文化类似于兄弟会。马萨利克会带着新员工在夜总会畅饮,有时还让客户带着模特回酒店。当Wirecard签下一家色情直播服务的客户时,马萨利克经常在办公室里玩《使命召唤》游戏的高管同事奥利弗·贝伦豪斯,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连接到电视上,并支付了一对一私人色情服务。他这么做时,是早上的十点半。
贝伦豪斯和另一名推销员指示屏幕上的一名赤裸上身的女子说:“摸摸你的鼻子”,以测试服务是否是真实直播的。这名女子遵从了他们的指示,这些男人们突然大笑起来,并下了更多订单,当时同事们都在。后来,“摸摸你的鼻子”成了办公室里的一个梗。
Wirecard的新任首席执行官是一位来自维也纳的看起来有点笨拙的高个子顾问,名叫马库斯·布劳恩。他缺乏马萨利克的魅力和亲和力,但他声称自己拥有社会和经济学博士学位,这给外界留下了他是一个安静但富有远见者的印象。

在他的领导下,Wirecard公司将其支付处理业务扩展到了在线赌博领域,这在一些司法管辖区是合法的,而在其他许多司法管辖区则是被禁止的。Wirecard通过收购其他国家的公司并通过它们进行支付,来规避当地法规。
后来一份重要的投资者报告指出,“通过授权第三方作为主要的处理器或收单机构,Wirecard没有被Visa或Mastercard直接识别。其中一些合作伙伴可能最终会失去自己的许可牌照,但Wirecard的许可牌照不受任何影响。”
这项业务的核心原则是,任何东西要想卖出去,就必须有一种支付方式。支付方式越少,费用就越高;法律风险越高,交易就越复杂。
2004年,施利希特格尔看到了机会,可以将Wirecard转变为一家上市公司,其股票可以在公开交易所交易。他买下了法兰克福股票市场上市的一家经营失败的电话服务供应商。在律师的帮助下,施利赫特格尔进行反向收购借壳上市,这样就可以在较少的监管审查下上市。
麦克鲁姆写道:“就像一个从内部吞噬宿主的寄生虫,Wirecard披上公司外壳,出现在股票市场上。”
第二年,在从市场上筹集到资金后,布劳恩安排Wirecard公司以大约1800万欧元的价格收购了一家德国小银行。在观察家们看来,布劳恩付出得太多了,公司只要花100万欧元就能申请到自己的银行执照。
但布劳恩的收购程序与股票上市一样,让公司在实现预期结果的同时避免了监管部门的审查,而监管审查很可能会导致失败。
投资者报告解释说,通过拥有一家银行,布劳恩“在线上和线下现金之间建起了一座桥梁”。对于Wirecard来说,1800万欧元并不是做生意的代价,而是获得做生意资格的代价。
——————–
2006年10月,美国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网上投注为非法行为,这对Wirecard的业务构成了生存威胁。大多数主要的支付处理商切断了其美国客户的赌博业务。然而,Wirecard利用了一个漏洞:法律允许“策略游戏”,理论上包括扑克。
2007年,公司收购了另一家支付实体,一家专门从事在线扑克的爱尔兰公司,并解雇了其审计师。这一年,Wirecard公司的收入激增了62%。施利希特格尔逐步出售了他在公司的全部股份。
Wirecard已经开辟了一个有利可图但比较脆弱的业务。主要的扑克公司开始抛弃Wirecard及其子公司,转而与经营状况更好的企业建立合作。与此同时,色情制品变得随处可得,而且是免费的。
2009年,尽管业务生存艰难,但布劳恩为投资者准备了一套不切实际的预测报告,显示利润和增长将呈45度直线上升,不久之后,首席运营官辞职了。
布劳恩任命当时29岁的马萨利克为新的首席运营官。马萨利克在不受监管的营养保健品(巴西莓粉和减肥茶)领域寻找新的骗子商业伙伴。
麦克鲁姆后来写道:“其计划是通过提供‘无风险’试用,来获取(客户的)信用卡或借记卡号码,然后用隐藏在小字号的费用说明来刺痛客户,而这些费用不太可能取消。”
Visa当时积极关闭与欺诈有关的账户,因此,根据麦克鲁姆的说法,马萨利克将付款分散在“许多不同的商家ID上,以保持投诉数量低于引起注意的门槛。” 但这并未奏效:Visa冻结了Wirecard的账户,并开出了超过1200万美元的罚单。布劳恩向股东隐瞒了这些事实。
此时,一位名叫托比亚斯·博斯勒的德国投资者,已经发现了Wirecard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违规行为。他最终怀疑公司还将非法赌博交易报告为合法交易,因此他让美国的一个朋友将钱转到一个与Wirecard有关的扑克网站。
博斯勒告诉我:“钱转到了扑克网站上,但在月度报表上却显示是一家法国的手机网店。”
2010年,美国政府指控一名居住在佛罗里达州的德国人洗钱,他与Wirecard有关系。他承认了一项较轻的指控,即进行无证转账业务,并声称不知道谁支付了他的法律费用。
仅仅通过故意错误编码,Wirecard公司至少洗白了价值15亿美元的赌博收益,而上述德国人用来自Wirecard银行的资金,向美国赌徒转移了大约7000万美元。当起诉的消息被公开后,Wirecard的股价下跌了30%以上。布劳恩宣布将业务转向亚洲。
——————–
2014年秋天,麦克鲁姆注意到,Wirecard在亚洲收购了许多无人听闻的小公司。官方的解释是,这些被收购的公司具有“当地优势”,Wirecard在“协同的基础上”帮助它们成长。
似乎没有人再关心佛罗里达州洗钱的指控了,公司直接否认存在任何关联,而投资大众也慢慢相信Wirecard拥有一个利润丰厚的亚洲部门,公司的股票市值飙升至40亿欧元。
在伦敦喝咖啡时,一位名叫利奥·佩里的对冲基金经理与麦克鲁姆分享了他的理论。Wirecard的主要商业模式是向公众撒谎,声称有巨大的利润,这样投资者就会推高其股价。
佩里说:“伪造利润最终会出现假现金的问题。到了年底,审计师会期望看到一个健康的银行余额,这是他们检查的第一件事。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些假现金花在假资产上。”亚洲的休眠空壳公司这时候派上用场,被包装成了有利可图的投资。
一周后,麦克鲁姆前往中东巴林首都麦纳麦,据说那里有一家名为Ashazi Services的公司,正在通过许可授权使用Wirecard的支付处理软件,费用为每年400万欧元。
麦克鲁姆在麦纳麦的第一天,就在寻找Ashazi的办公室。但在登记的地址没有找到它的踪迹。第二天,他出发去找Ashazi的公司律师库梅尔·阿拉维,他的办公室位于一家炸鸡店后面一条垃圾遍地的小巷里。
一个人挥手让他进去,告诉他阿拉维已经不在那里工作了。但他有阿拉维的电话号码,在一个简短的电话之后,麦克鲁姆被指引到一个空的停车场。阿拉维乘坐一辆布满灰尘的汽车抵达。
他说:“大楼还在盖,没人能找到它(Ashazi Services)。”
他和麦克鲁姆走近一个建筑工地,走进了一间似乎唯一有人的办公室——白色的墙壁、廉价的家具和几棵蕨类植物。
“Ashazi, Ashazi ,”阿拉维喃喃自语,好像他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他拿出一个文件夹,里面有一些注册文件,并建议麦克鲁姆打电话给那个被列为Ashazi创始人的女人,她是当地的一名演员和电视节目主持人。
麦克鲁姆通过电话联系到了她,但她不记得Ashazi的合同,并建议他问问她在菲律宾的商业伙伴。这位商业伙伴听说过Ashazi,但他说他只参与营销。他以为这位女演员在经营公司。
麦克鲁姆的结论是,Ashazi在网上的存在“充满了谎言”,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阿拉维派声称,不记得麦克鲁姆。)而且,据麦克鲁姆从文件中了解到,其从未支付授权费给Wirecard。
回到伦敦后,他把自己的发现交给了《金融时报》的特稿编辑。但编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它,”金融时报博客Alphaville的创始人保罗·墨菲告诉我。
他说:“和《卫报》或《纽约时报》不同,《金融时报》没有调查报道的传统。”他接着说,印刷出来的故事(报纸版)“必须让所有读者都能理解”,而“Alphaville已经抛弃了这个想法。我们做的是非常非常硬核的金融报道。”
墨菲把麦克鲁姆拉进了他的团队。墨菲对我说:“我需要一个具备拆解资产负债表的核心技术能力的人。”尽管麦克鲁姆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在报纸的报道中使用“欺诈”一词,但据他回忆,墨菲鼓励麦克鲁姆,“就把Alphaville作为一个平台,来消除你的怀疑。”
由此产生的系列《Wirecard屋》(House of Wirecard)于2015年春天发布。但即使是Alphaville精通金融的读者,也难以理解这些材料。一位读者评论道:“这篇文章可以用一段话,用简单的英语说明作者的观点。报道中有很多事实,但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Wirecard的回应没有那么模棱两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它花了很多时间试图制造这样一种印象:它是卖空者(股市暴跌时卖空者就能赚钱)和记者(他们被卖空者收买了)犯罪阴谋的受害人。
2016年,伦敦的两名卖空者发布了一份名为《扎塔拉报告》(Zatarra Report)的匿名调查报告,报告长达100页,指称Wirecard存在一系列犯罪活动。报告偶尔会转向阴谋论,这些理论没有得到证实或根本不真实。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Wirecard花费了近40万欧元聘请私人侦探,揭露和羞辱报告的作者。不久,他们的电子邮件收件箱里就充斥着钓鱼链接和同性恋色情片。他们的通信记录被黑了。
在麦克鲁姆报道了《扎塔拉报告》后,他也成为了攻击目标,很快他就被逼到了偏执的边缘:他开始记录车牌号,检查树篱笆上的摄像头,睡觉时床下放着锤子。
这不是Wirecard第一次追究批评者;2008年,公司威胁了慕尼黑的投资者托比亚斯·博斯勒。他曾押注Wirecard股价下跌,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的头寸,但Wirecard的一名律师还是设法找到了他。
他说:“我接到一个律师的电话,说‘你做空了Wirecard’。他开始念出我的交易。他说了日期、时间戳、股份数量——他有我交易的所有细节。”
几天后,律师和两名土耳其拳击手来到了博斯勒的办公室。拳击手们把他逼到墙角。其中一个猛击了他脑袋旁边的墙壁;另一个威胁他的生命。
博斯勒吓坏了,平仓了他的空头。他向德国当局提供了有关Wirecard洗钱活动的信息,但一直杳无音信。
他说:“除了丹·麦克鲁姆,没有人仔细调查过Wirecard。”
——————–
墨菲对我说:“人们对金融有这样的看法:金融就是衣着光鲜。”但是,根据他的经验,体面的外表通常在银行门口结束。
在英国,赌博所得不需要缴税,因此投机者们创造了一个平行市场,利用小道消息和内幕信息进行交易;他们使用一种被称为“点差交易”的策略,就是在不持有任何公司股票的情况下,对股票价格的涨跌进行赌博。
他们进行保证金交易,并经常爆仓。墨菲告诉我:“这些人可能今天身价2000万美元,明天就一钱不值了。”正是在这里,在他亲切地称之为“土匪”的这群人中,他找到了许多最好的消息来源。
他在他最喜欢去的Sweetings餐厅吃着香槟和鱼三明治的午餐时说:“他们中的很多人真的有点粗鲁,但他们有数学头脑,可以计算数字,也可以计算概率。”
现年60岁的墨菲报道伦敦金融领域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他接电话时仍然会报出自己的姓氏,就像在没有来电显示的固定电话上一样。
2016年,他接到了一个“土匪”打来的电话,他来自埃塞克斯,是一名商人、点差投机客和夜总会老板,名叫加里·基尔贝。
基尔贝问道:“你们写的关于Wirecard是什么东西?你确定这是真的吗?”
墨菲回答说:“当然他X的是真的。”
基尔贝说:“有个人说这都是错的。他不喜欢丹。他想和你谈谈。”那个人叫扬·马萨利克;他让另一位价差交易投机者(此人此前已承认犯有证券欺诈罪)雇用基尔贝作为中间人。
墨菲说:“叫他滚。”
几乎过了两年,马萨利克才再次主动联系墨菲。同样是通过间接接触;墨菲的另一位线人在吃龙虾意面的午餐时不经意地向他提到,如果他停止发表有关Wirecard的报道,马萨利克会付给他“一大笔钱”。
那人说:“我是认真的,我听说他会出1000万。”
马萨利克想和墨菲共进午餐,他会从慕尼黑飞过来,基尔贝和他的儿子汤姆也会出席,汤姆曾是电视真人秀明星。马萨利克向基尔贝父子每人支付了10多万英镑,作为这顿饭的中间人。
几周后,墨菲走进海德公园附近的一家牛排馆,身上装着麦克风,希望能抓到马萨利克在行贿的证据。他没有团队支持:墨菲的三名同事,本应用藏在手提包里的摄像机拍摄这段互动,但马萨利克在最后一刻改变了地点。
马萨利克坐在桌旁,穿着一套蓝色西装。他热情地向墨菲打招呼。和牛牛排,苏打水,美酒。马萨利克想让墨菲知道,根据他的经验,记者很容易被收买。
但他说话小心翼翼;没有明确的提议。有一次,马萨利克暗示墨菲和麦克鲁姆处于监视之下,并指出他的“朋友”向他报告说,这两个人过着“非常普通的生活”。
墨菲怀疑另一个用餐者(一个独自坐着的男人),正在进行反监视。墨菲说,当账单来的时候,马萨利克用一张金色的信用卡付账。
墨菲告诉我:“他显然很有趣——他认识很多人,而且到处撒钱。所以我开始开发马萨利克作为潜在的资源。”
在另一次午餐中,墨菲承诺,金融时报不会再根据Wirecard过去的轻率行为发表更多的报道,马萨利克向墨菲发誓,公司没再做什么出格的事了。他们握了握手。
墨菲走出餐厅后,加里·基尔贝对马萨利克说:“听着,如果你在撒谎,保罗会发现的。他一旦发现,你就玩完了。”
——————–
在墨菲看来,马萨利克的许多活动都与俄罗斯政府有某种联系,这似乎很重要。Wirecard在那里没有业务,没有子公司。但马萨利克经常去俄罗斯,经常乘坐私人飞机,有时午夜后降落,黎明前离开。
据调查机构Bellingcat报道,他的国际旅行受到俄罗斯主要安全机构FSB的密切监控。“他的移民档案有597页,比我们在5年多的调查中遇到的任何外国人的档案都要多,”Bellingcat的俄罗斯首席调查员在多年后报告说。
在慕尼黑,马萨利克用一系列俄罗斯军帽和一套俄罗斯套娃装饰了他的办公室,这些套娃画着过去一个世纪的俄罗斯领导人,从矮小的列宁到臃肿的普京。他还在俄罗斯驻慕尼黑领事馆对面的一座豪宅里举办秘密聚会,他以每年68万欧元的价格租用了这座豪宅。
在维也纳,马萨利克和布劳恩与公开持亲俄观点的极右翼政客混在一起。两人都成为了一个名为奥地利-俄罗斯友谊协会的组织的付费会员,并与其秘书长弗洛里安·斯特尔曼建立了业务往来。
2015年底,斯特尔曼要求Wirecard公司向协会捐赠2万欧元,以帮助支付其15周年纪念晚会的费用,晚会名为“来自俄罗斯的爱”,是一场奢华的通宵晚会,由空中飞人和普京模仿者表演。马萨利克同意了,但要求将Wirecard的名字从企业赞助名单中删除。
2016年,马萨利克协助俄罗斯雇佣军部署到利比亚。一位曾与Wirecard合作创办电子支付初创公司的美国商人,在班加西附近投资了一家水泥厂,他需要清除未爆炸的战争残留物。马萨利克推荐了他的一个俄罗斯朋友斯坦尼斯拉夫·佩特林斯基,他是一家安全公司的高管。
佩特林斯基的公司,即R.S.B集团,清除了水泥厂400多枚炸药。但这一安排后来一直困扰着这位美国商人:在穆阿迈尔·卡扎菲死后的混乱中,这是俄罗斯首次在利比亚地面部署武装部队。
R.S.B的雇佣兵在水泥厂前摆姿势拍照,他们举着一面横幅,上面写着“我们不是天使,但我们在这里”。
詹姆斯敦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谢尔盖·苏克汉金曾研究过俄罗斯雇佣军的行动,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R.S.B集团在利比亚的活动“应该被视为经济利益和情报收集/监视的结合,这些本可以用来为更‘严肃’的参与者做好准备。”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俄罗斯加强了与利比亚指挥官在此地区的关系,并从瓦格纳集团部署了大约1200名士兵。他们占领了油田,扩大了俄罗斯的安全足迹,并影响了非洲的经济和政治事务。
当时,俄罗斯的军事和情报行动在欧洲日益活跃。发生了多起暗杀和可疑的死亡事件:政府的目标人物不是从窗户掉下来,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枪杀。
然后,2018年3月4日,两名俄罗斯军事情报官员前往英国小城索尔兹伯里,携带了一个伪装成香水的小瓶子。他们在叛逃到英国的前俄罗斯高级情报官员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家中的前门把手上,喷洒了里面的东西;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人们发现斯克里帕尔和他的女儿尤利娅在公园的长椅上失去意识,他们无法控制地抽搐,口吐白沫。
英国化学武器分析人员确定,这种物质是诺维乔克(Novichok),这是苏联军事情报机构几十年前设计的一种致命神经毒剂。作为回应,英国驱逐了23名俄罗斯外交官,他们被怀疑是情报官员,并对另外14名俄罗斯流亡者和商人在英国的死亡展开了调查。
那年秋天,马萨利克又把墨菲叫到德国,在一间私人餐厅共进午餐,递给他一叠文件。这些文件包含了俄罗斯政府对联合国化学武器机构的官方谈话要点,对英国对斯克里帕尔中毒事件的调查提出了质疑。
这些标记为机密的文件还包含诺维乔克的化学配方。
墨菲问道:“你从哪儿弄来的?”
马萨利克笑着说:“从朋友那里。”
——————–
2018年8月,Wirecard的市值为280亿美元。公司将德国商业银行挤出了德国最负盛名的DAX 30指数成分股。
布劳恩拥有公司8%的股份,名义上已经是亿万富翁了。他以自己持有的Wirecard股份为抵押,从德意志银行获得了1.5亿欧元的个人贷款。据举报人透露,马萨利克似乎从公司骗取了数千万欧元(如果不是数亿欧元的话)。
据报道,Wirecard拥有5000名员工,正在处理25万商户的付款,其中包括大型航空公司和连锁杂货店。布劳恩告诉投资者,他预计销售额和利润将在未来两年内翻一番。
如一位德国记者后来所说,在科技会议上,布劳恩被誉为“阿尔卑斯山上的史蒂夫·乔布斯”,他说Wirecard的商业优势来自其专有的人工智能。

拥有计算机科学背景的布劳恩说:“这不是关于拥有数据,而是关于从数据中传递价值的算法。”但当时这家公司没有人工智能;大多数Wirecard账户,都是通过电子表格手动拼凑起来的。
作为一家没有分支机构的银行,Wirecard把现金存放在办公室的保险箱里,有时会把钱藏在杂货袋里,分发给商业伙伴,总金额达数十万欧元。
当墨菲对马萨利克与俄罗斯安全部门的联系感到困惑时,麦克鲁姆有了一条新的调查线索。Wirecard驻新加坡亚洲分部的首席律师帕夫·吉尔辞职了,同时带走了70G的电子邮件。
正当他苦思如何处理这些材料时,他得知母亲曾给麦克鲁姆写过信。
吉尔知道后说:“我的天哪,妈妈,你做了什么?”
不久之后,麦克鲁姆飞往新加坡收集泄露的数据。两人在一个公共喷泉附近会面,以屏蔽监听设备。麦克鲁姆复制了文件,回到了伦敦。接下来的六周,他在金融时报总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工作,试图在数十万封电子邮件和日程表预约中追踪个人欺诈行为。
“驱使我前进的是扬·马萨利克,”麦克鲁姆后来在他的书中写道。他们从未说过话,也从未见过面,但麦克鲁姆可以从文件中看到,“他总是若隐若现,有时发出命令,但更多时候他的指示是间接传达的,他的参与总是会带来谜团:以‘因为这是扬的一家公司(作为解释的借口)。’”
每天晚上,麦克鲁姆的脑子里都是新的数据、名字和组织结构图,离开办公室前,他把笔记本电脑锁在保险箱里。
当年早些时候,Wirecard亚洲金融团队的一名女性紧张地找到吉尔,报告说她的老板埃多·库尼亚万(马萨利克是他的上司)做了一个演讲,在演讲中他教员工如何犯下严重的金融犯罪。
库尼亚万后来在新加坡被控金融犯罪;他是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的对象,下落不明。
库尼亚万用白板和记号笔勾勒出了“返程投资”的做法,即根据需要在几个地点之间转移一定数额的资金,以欺骗不同辖区的审计人员,使他们认为每个本应不相关的账户都资金充足。
据报道,Wirecard的审计机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依赖的是公司提供的文件和账户截图,而没有与公司的银行核实数据。
吉尔联系了他在慕尼黑的主管,主管让他委托进行内部调查,结果发现了返程投资、倒签合同和其他非法计划的例证。
但当调查结果传到Wirecard董事会时,这些担忧被打消了。Wirecard的副总法律顾问在一款加密通信应用上给吉尔写道:“我认为扬非常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但他们不会被人抓住把柄(they don’t shit in each other’s bed)。”几个月后,吉尔被告知,如果他不辞职,就会被解雇。
到2019年1月30日上午,这个故事已经完成,可以在金融时报上发表了。麦克鲁姆向Wirecard发送了问题,并等待公司的回复。
午餐时间,保罗·墨菲去Sweetings吃了一份螃蟹三明治,喝了一杯白葡萄酒。然后加里·基尔贝打来电话。
一位经纪人在基尔贝夜总会楼上的办公室前停了下来,告诉他,一个很受欢迎的价差交易账户正在“做空Wirecard”。伦敦金融界的热门传言是,《金融时报》将在下午1点发表一篇热门文章。
基尔贝说:“你们他X的走漏风声了。”
墨菲冲回了金融时报总部。他喊道:“我们他X的走漏风声了!”
——————–
这个消息是怎么泄露的?麦克鲁姆和墨菲采取了非同寻常的预防措施,只会当面谈及这个故事,从不在电话中讨论。这篇报道甚至没有被上传到联邦调查局的内部系统。
但基尔贝的一个细节是错误的:《金融时报》计划在当天下午发布报道,但一直没有确定具体时间,下午1点是它给Wirecard的评论期限。除了公司自己,似乎不可能有其他人披露信息。
墨菲走到路透社的终端机前,调出了Wirecard的股票行情。他告诉我:“我们坐在那里看着股价在接近一点钟的时候开始下跌。然后没看到任何报道发布,于是人们开始买进。” 他们又等了两个小时,等待Wirecard的答复。然后,正如墨菲所说,”点击发布之后感觉要吐了。”
文章标题是“伪造的合同”,副标题是“伪造的账目”。这篇文章只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就让Wirecard蒸发了50亿欧元的价值。两天后发表的一篇后续文章又使其损失了30亿欧元。
德国的反应是反射性的防御,仿佛《金融时报》的报道是对德国本身的攻击。德国商业银行的一位股票分析师在给投资者的信中写道:“麦克鲁姆的另一篇假新闻文章。”股价的任何下跌都是“一个买入的机会”。
德意志银行监事会的一名成员给布劳恩写道:“我在《金融时报》上看到,你是一个多么顽皮的孩子。”他加了一个眨眼的表情符号,并说他刚刚买了Wirecard的股票。“真想把这家报纸灭了!!”
2019年2月18日,德国的金融监管机构联邦金融监管局以Wirecard公司“对经济的重要性”为由,发布了禁止创建新的空头头寸。一位德国议员后来说:“就在那一刻,他们站到了犯罪分子一边。”
同一天,慕尼黑的检察官向一家德国报纸证实,他们已经开始进行刑事调查。但他们并不是针对Wirecard,而是针对《金融时报》。
——————–
在一个正常运作的市场中,卖空的规模往往与有关的财务违规行为的恶劣程度相关。一位名叫法赫米·奎迪尔的年轻基金经理,在联邦金融监管局禁止卖空后写道:“我们进行了数百甚至数千小时的尽职调查。”这种调查包括访问办公室和监测卫星图像,以了解在中国的一家工厂的活动是否真的存在。
奎迪尔说:“人们认为,投资者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看图表和数据上。但公司不仅仅是这样,企业的核心是人。高管们被一系列的情感因素和压力所驱动。单从财务报表中不足以看出这些因素。”
奎迪尔在长岛长大,是孟加拉国移民的二女儿,在大学里学习生物和数学,然后在金融业找到一份工作,但她对这个行业基本上持蔑视态度。
作为一个对冲基金的研究员,奎迪尔调查并最终促成了一个药品价格欺诈行动的终结,这为她赢得了刺客的绰号。她不下长注,只对她认为从事犯罪活动的公司下短注。
她说:“归根结底,掠夺性、欺诈性和犯罪行为对企业不利。”她认为她的作用是揭露欺诈行为,并从中获利,她说:“这是一种颠覆性利用资本主义和资本市场的方法,是介于公民义务和革命行动之间的做法。”
2018年1月,奎迪尔在曼哈顿的一个联合办公空间成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她将其命名为Safkhet Capital,是为了纪念埃及的数学女神,并雇用了唯一的员工克里斯蒂娜·克雷曼蒂,她最近在耶鲁大学学习了一门由吉姆·查诺斯( 上文提到过)教授的欺诈历史课程。
那时,Wirecard已经收购了花旗集团的北美预付借记卡项目。在奎迪尔看来,这是一个鲁莽的举动。如果公司正在犯罪,那么这种行为现在蔓延到了美国本土。
墨菲告诉我:“在全球范围的金融领域,存在一种情况:唯一有效的警察是美国人。我们的监管者在吃午饭,大多很无能。你会发现,比如说,在伦敦,你可以成为一个骗子,从世界各地的人那里偷钱。只要你不偷英国境内人的钱,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2019年初,奎迪尔和克雷曼蒂坐着后者的2002年大众敞篷车出发,前往Wirecard的美国总部,其注册在费城外宾夕法尼亚州康舍霍肯一个办公园区。在5040室,他们找到了一个足以容纳600名员工的办公空间,但那里只有几十个人。
一个迎接她们的人向她们出售预付卡,里面装着高达15万美元的资金,并补充说,她们完全可以将这些卡分发给其他人。奎迪尔和克雷曼蒂惊呆了。奎迪尔告诉我:“暗网上都找不到超过1万美元的预付卡。”
奎迪尔和克雷曼蒂在支付行业中积累了秘密消息来源,并提出了一个工作理论:Wirecard公司的主要商业目的,是为有组织的犯罪网络和俄罗斯寡头提供服务,即成为“大规模洗钱活动的一站式”场所。
她们在给Safkhet投资者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这些活动需要具备一定规模来支持每年数十亿的脏钱。”Wirecard的银行执照是关键所在,这使得公司既能接受犯罪资金,又能掩盖其来源。
——————–
对于Wirecard的领导层来说,德国对《金融时报》展开的刑事调查在预料之中。马萨利克就提供了第一个证人。三年来,他一直与基尔贝的儿子汤姆保持着联系。
基尔贝告诉我:“那是一段相当困难的时期,杨向汤姆承诺了整个世界。”这种操作得到了回报。汤姆当时正在他父亲的办公室里,马萨利克走进来,分享了《金融时报》在下午1点发表其评论文章的谣言。
汤姆又向马萨利克汇报了这个消息,马萨利克想要所有在场的人都提供书面陈述。基尔贝回答:“你X的别想把我拖下水。”但基尔贝女儿的男友因为贩毒团伙洗钱而刚刚出狱,他目睹了这一幕,并提出要提供一份声明。
2019年2月,马萨利克会见了慕尼黑最高检察官希尔德·鲍姆勒·霍斯勒。他告诉检察官,作为“敌方侦察员”,他花了几年时间潜入伦敦的点差交易,并说《金融时报》与卖空者勾结在一起。
三天后,霍斯勒向德国媒体发表了一份声明:“我们从Wirecard公司收到了确实信息,新的空头攻击已在规划中,并将利用大量资金来影响媒体报道。”
这并不是马萨利克采取的唯一防卫行动。Wirecard公司与Arcanum全球情报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这是一家战略情报公司,其领导层由前英国、美国、法国和以色列高级情报和军事领导人组成。Arcanum的代表坚持认为,公司为Wirecard提供的服务只包括对吉尔泄露新加坡分公司机密信息的内部调查。
但是在2月5日,也就是麦克鲁姆关于Wirecard亚洲分部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后的几天,Arcanum的创始人罗恩·瓦希德向马萨利克发送了一份名为太阳神计划(Project Helios)的提案,以“调查和识别卖空者”,并实施一个多阶段的“攻击计划”。
尽管Arcanum的领导层声称此提案从未被执行,但公司写给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的一封信中说,Arcanum “被Wirecard聘请来调查一系列的卖空攻击”。
提案称,“第一阶段将是一个‘范围界定和披露阶段’,审查所有现有信息和初步情报结果。”下一阶段将包括“更有针对性和深入的情报收集和分析”,目标的“错误行为和弱点”将被“审慎地追查”。
正如Arcanum所说,只要每月支付20万欧元的费用,前“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和执法机构的高级领导人”将部署他们的综合网络和专业知识,为Wirecard服务。
麦克鲁姆继续调查Wirecard在亚洲的活动。其全球销售额的一半似乎来自于三个客户:一个在迪拜,一个在新加坡,第三个在菲律宾,叫做PayEasy。麦克鲁姆的同事斯特凡尼亚·帕尔马前往马尼拉,调查PayEasy。其所谓的总部原来是与一家巴士公司共用的。
另一个Wirecard的合作伙伴ConePay则是在一个被稻田包围的偏远村庄的私人住宅。迎接帕尔马的是两个菲律宾人,他们正在给一只小白狮子狗和一只博美犬梳理毛发。他们都没有听说过ConePay。
然后,一位家庭成员拿出几张邮件碎片。其中一份是Wirecard银行的文件,收件人是ConePay International,显示有30欧元的余额。
现在,马萨利克已经完全扎根于他的俄罗斯雇佣兵朋友斯坦尼斯拉夫·佩特林斯基的事务中。Wirecard公司与R.S.B.集团在迪拜的控股公司安排了一项交易,向雇佣军出售其预付借记卡软件。
在与Wirecard财务团队高级成员达格玛·施奈德的加密聊天中,马萨利克写道,如果审计员对R.S.B.有疑问,他们应该打电话给普京。在麦克鲁姆和帕尔马逼近菲律宾的欺诈案时,马萨利克与施奈德开玩笑说,有人“被R.S.B.的俄罗斯雇佣军射杀”。
接下来的一周,他写信给施奈德说,他“从早上5点开始就一直在与《金融时报》战斗”。
施耐德回答:“把你的俄国军送到伦敦去,他们应该可以让我们获得一些安宁。”
麦克鲁姆和帕尔马在3月28日公布了他们对Wirecard合作伙伴的调查。两周后,联邦金融监管局以 “涉嫌操纵Wirecard股票市场”为由对他们提出了刑事指控。外部投资者将德国政府的行动视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4月下旬,经营着世界上最大的科技风险投资基金的日本公司软银向Wirecard投资10亿美元,以换取可转换为5.6%股份的债券。但《金融时报》的报道仍然让软银的团队感到震惊,他们要求查看Wirecard在亚洲最大的客户名单,而马萨利克对此进行了伪造。
——————–
Wirecard把每一个做空者都当作生存的威胁。2016年,马萨利克曾找到基尔贝在伦敦点差交易中的另一位联系人尼克·戈德,并向他提供了300万英镑,以说服一位有钱的朋友停止做空Wirecard。
戈德拒绝了,他说他发现马萨利克很无聊,并认为他拿咖啡杯的方式表明他是“一个失败者”。戈德说,只有一个腐败的公司,才会派一个高级管理人员去追捕其批评者。
三年后,名为乔恩的英国前卧底警察(现在是一名私人侦探)被雇来为一名客户工作,他在伦敦的多切斯特酒店设立了临时住所。
这位客户身材很好,头发剪得很短,胡茬均匀。他有利比亚背景,但在法国长大,英语无懈可击,用高面值的纸币给酒店员工发小费。乔恩告诉我:“他想在英国时对自己进行反监视,以确保没有人跟踪他。”
乔恩不喜欢“私家侦探”这个词,因为他认为这会缩小他的工作范围。他平均每天通过公共部门的联系人,收集5到10个目标的旅行记录和警方档案。
他们不知道他的全名——他们只知道不能问问题,而且他们会得到现金报酬。他的客户包括企业、政府机构和亿万富翁,他的职责范围从监视调情的配偶,到帮助国际犯罪团伙确保可以用偷来的护照把杀人犯送出边境。
他说:“我能做的,我做过的,有很多非常值得怀疑的事情。当警察时,你必须有道德,或者你注定要有道德。这就是当警察的意义所在。在私营部门,老实说,这真的不重要。”
在将近4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坦率地娓娓道来,条件是我既不公布他的全名,也不描述他的外貌。
多切斯特酒店的客人自称拉米,但乔恩不懂他的业务。几个月后,乔恩找到了这个人的全名拉米·埃尔奥贝迪(Rami El Obeidi),并了解到他在革命期间曾短暂担任利比亚过渡政府的外国情报主管。
和马萨利克一样,埃尔奥贝迪也穿着高端意大利服装品牌,在前军事和情报官员的陌生世界中游刃有自如。他显然是Wirecard的主要投资者,也是马萨利克位于俄罗斯驻慕尼黑领事馆附近秘密豪宅的常客。
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埃尔奥贝迪来到伦敦,亲自负责一项情报工作。调查的主要目标是尼克·戈德,他与麦克鲁姆一起被联邦金融监管局指控为嫌疑人。
戈德卖工业用品赚了一大笔钱,他把钱押注在他认为有优势的地方。他英俊英俊,身材健硕,一头乌黑飘逸的头发。四十多岁的他慷慨大方,富有魅力,在伦敦、迈阿密和戛纳的豪宅里吸食大量可卡因,用纸牌戏法让客人眼花缭乱。
他告诉我:“我17岁的时候经常去牛津街,去骗人,会有像你这样的傻瓜来,你会输的。”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他被禁止进入赌场数牌,也被禁止与骑师一起下注赛马。
有一次,他在赌一场足球比赛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到达第一个界外球之前,买通了一名球员,让他在比赛开始的几秒钟内把球踢出界外。他坚持说:“如果我知道结果,这就不是赌博,我从不赌博。我从来没有打过一场我认为自己会输的比赛。”
墨菲在基尔贝的60岁生日派对上认识了戈德。在那次喧闹的聚会上,基尔贝敦促他的客人“能喝多少就喝多少”。墨菲听说戈德是Soho区一家高级歌舞俱乐部“盒子”(Box)的共同所有者,据说俱乐部的女主人在欢迎客人参加凌晨1点的滑稽歌舞杂剧时,指示客人“爱干嘛干嘛”,“尽你所能吸食可卡因”。

戈德还记得那次见面,墨菲给了他自己的电话号码,并邀请他如果有什么有新闻价值的线索可以打电话给他。墨菲回忆起一些更有帮助的事情:“我想派一个年轻的金发女记者去收集他的废话。”
一天,戈德打电话给墨菲,向他推销一篇关于一家体育博彩公司的报道。但墨菲告诉他,他没有时间讲电话,他正忙于Wirecard的事情。
尔德回忆道:“当他说‘我被Wirecard困住了’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这是一个不用动脑筋的情况了。我将用生命做空这家公司。我这么做了。”
那年夏天,埃尔奥贝迪和戈德共同认识的足球经纪人赛义夫·鲁比,在戛纳的一次聚会上偶然遇到了戈德。据他回忆,当时戈德“在桌子上跳舞,像个疯子一样,我也玩得很开心”。
鲁比找到他,说他在为一个外国投资者集团工作,他们希望投资数十亿美元。戈德邀请鲁比在接下来的一周,把投资者带到他在伦敦的办公室。
2019年7月17日上午,鲁比走进了戈德的办公室,陪同他的是一名自称代表外国投资者的兰开夏郡男子。事实上,他是为埃尔奥贝迪工作的私人情报人员,随身携带着隐藏的录音设备。
戈德建议做空Wirecard,声称《金融时报》即将发表一篇报道,会让Wirecard的股价跌至零。“可能是明天,可能是——你永远不知道,”戈德说。他向他们保证,这条消息是可靠的:他的消息来源是调查编辑保罗·墨菲。
巧合的是,戈德的时机选对了。会面几小时后,麦克鲁姆向Wirecard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透露他知道公司在迪拜的大部分业务都以假客户为中心。马萨利克已经从埃尔奥贝迪那里收到了戈德的录音副本,他召集了一位公关专家,后者建议他们将录音和麦克鲁姆可疑的提问时间分享给德国《商报》的调查主管松克·伊沃森。
这位来自兰开夏郡的私家侦探就“深层背景”与伊沃森进行了交谈,以提供细节,但没有透露姓名。他提到他一直在为Wirecard的一位投资者工作,但没有提到这位投资者曾是一名利比亚间谍。
Wirecard的律师写信给金融时报,称Wirecard向英国和德国当局提供了尼克•戈德和保罗•墨菲之间内幕交易的证据。这封信要求金融时报在调查完成之前不要发表任何Wirecard的报道。
墨菲立即给戈德发短信,告诉他自己被录音了。《金融时报》的编辑莱昂内尔·巴伯对墨菲说:“保罗,你是一个出色的记者,但你刚刚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
墨菲向巴伯交出了自己财务状况的全面审计。但这还不够;报社的声誉岌岌可危。
巴伯告诉我,四年来,“我一直对合规人员和律师说,‘滚开,我们正在做这个报道,’但当这件事发生时,我必须做点什么。”他聘请了外部律师调查墨菲和麦克鲁姆。他对墨菲说:“你将不得不在罪恶箱里呆上一段时间。”
——————–
Wirecard现在胆子大了,将法律授权给了Arcanum公司的高管,让他们“以任何他们认为必要和合法的方式”代表其行事。
Arcanum当时的副总裁基思·布里斯托曾担任英国国家犯罪局的首任局长,他会见了金融行为监管局,作为Wirecard让此机构调查金融时报的努力的一部分。金融行为监管局拒绝就其与Arcanum的关系发表评论。
Arcanum的领导层包括一位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和一位前英国陆军参谋长。即使在不清楚所分享信息的来源的情况下,这些人也在利用人脉打探。尽管Arcanum团队显然从未听说过埃尔奥贝迪,但他们给英国当局写了一封信,声称自己对埃尔奥贝迪对戈德实施诱捕行动前的“事件和相关主题”有“相当多的了解”。
那年秋天,埃尔奥贝迪雇佣了28名特工前往伦敦街头,执行一项名为“Palladium”的任务。地面小组由前军情五处官员海莉·埃尔文斯领导,特工们通过私人对讲机频道相互沟通。其中很多目标都是伦敦的卖空者。乔恩现在被派去跟踪戈登。
一次又一次,乔恩因为对行动了解太多,开始质疑自己在其中的角色。他告诉我:“如果只有我们六个人看着他,我也会随大流。现在回想起来,从某些方面来说,我真希望我当初这么做了。”
这个小组被指示只使用法律允许手段,以便收集到的任何情报都能在法庭上站得住脚。但Palladium行动给人兴师动众的感觉。它每天的运行费用为1.8万英镑,采用了乔恩所见过的最全面、最具敌意的监视手段。
乔恩谈到戈德时说:“我为他感到非常难过,你知道,我还是有良心的。”
一天,乔恩用一次性手机给戈德的管家打了电话。他说他是警察,需要戈德就一项正在进行的调查给他打电话。戈德几乎立刻回电。
乔恩告诉他:“他们正在对你进行大规模监视。我觉得你在这里会被弄死的,真的。”
戈德把乔恩叫到办公室。他说:“你知道,我在这行待了很长时间,知道什么时候有人在吸食可卡因。戈德当时嗨了。他说,‘对!保罗•墨菲是我在《金融时报》的联系人之一。你得告诉他监视行动的事!’”
他们去伦敦一家高档酒店克拉里奇酒店见墨菲。乔恩向他提供了Palladium行动的文件,并告诉他他所知道的运作结构。
墨菲要求乔恩证明他的权限和身份。这时,乔恩想起,在之前的一份工作中,他曾监视过另一位金融时报记者,是墨菲团队里的卡迪姆·舒伯。
墨菲回忆说,过了一会儿,“他给我发了一张卡迪姆妈妈护照的照片!”
乔恩告诉我:“我笑了。”他还有舒伯的银行卡复印件。“但我并不是想炫耀。我当时就想,这世界真小啊!这有多好笑!我正在和保罗·墨菲聊天,他坐在卡迪姆对面,我走过去看了他一眼,发生这事的可能性有多大?我觉得这很讽刺,真的。”
现在墨菲找到了前军情五处官员埃尔文斯,她负责埃尔奥贝迪的地面行动。
“我试着去吓唬她,不幸的是,我是在晚上11点左右这么做的,当时我已经喝了几杯酒。”他给埃尔文斯发短信说,他可以“看到我们即将对你们公司造成的损害”,并补充说,“和我合作,我保证不会耍你。”
她的答复是她的律师诉状。巴伯把墨菲叫到办公室,墨菲提出辞职。当巴伯拒绝他的提议时,墨菲变得挑衅。“你知道,这些故事——它们不是从他X的窗户飘进来的!”他喊道。
巴伯回答说:“保罗,我要把这个该死的骗子绳之以法,我想听故事。但不是说你在晚上11点给某个前军情五处特工发短信的故事!”
两个月后,外部律师事务所洗脱了墨菲和麦克鲁姆的罪名。整个夏天,他们都在悄悄地准备报纸的最后一击—— 一篇直截了当的文章,提供了确凿的欺诈证据,并包括了Wirecard的所有基础电子表格和电子邮件。莱昂内尔·巴伯的指示是“让他们见血”。
这篇文章发表于2019年10月15日。墨菲回忆说:“我们当时想,我们干掉了它,就这样。”
故事情节糟糕至极,以至于投资者要求进行法务审计,Wirecard默许了。但调查将持续6个月,Wirecard的首席执行官布劳恩向股票分析师保证,调查将消除所有担忧。
在这个节骨眼上,“该死的股价居然上涨了,”墨菲说。“德国的每个人都在说,‘哦,是啊,金融时报说的全是废话。’而且,在这个时候,像尼克·戈德这样的人实际上都疯了。他精神病发作了。他被发现时已濒临死亡,倒在方向盘上。
戈德说,他把酒精和阿普唑仑(镇静剂)混合在一起,停在路边睡了个午觉。
墨菲接着说:“没人知道该相信谁,整个社区都认为Wirecard是一个骗局,到那时,这已经是一个大规模的社区了,每个人都他X的对其他人充满了怀疑。”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对卖空者的攻击越来越个人化,甚至变得暴力。法赫米·奎迪尔在上西区遛贵宾犬时,被一名蒙面男子用铜指关节猛击头部;她被打晕了,袭击者什么也没偷,也没被找到。
似乎特工们正在收集尼克·戈德交易的详细信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所有的杠杆赌注都被平仓,损失高达数千万英镑。
戈德回忆道:“我的名声被玷污了。银行现在一夜之间就把我拒之门外,我妻子离开了我。”
一天晚上,他告诉我:“我在Box吸可卡因,我疯了,我像个疯子一样喝酒,我和你见过的最性感的女孩走出去,10分满分我打15分。”但这是一个陷阱;一封敲诈勒索的联络录音,通过电子邮件随后寄来。
已经清醒的戈德说:“最糟糕的是,我的袜子一直没脱。在我这个年纪,你不会想被看到穿着白袜子乱搞的。”
——————–
在Wirecard倒闭的前一年,也就是2020年6月,公司领导层策划了对德意志银行的收购。这笔收购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Wirecard的资产负债表欺诈可能会被埋在这笔交易中。
墨菲说:“这基本上是布劳恩最后一次掷骰子。”
Wirecard的绝望还在继续。审计人员重点关注了菲律宾的两个银行账户,据称这两个账户持有失踪的20亿欧元。新冠疫情的限制使审计人员亲自访问银行的能力受限,因此据报道,Wirecard聘请了菲律宾演员,在假的银行小房间里,在视频电话中证明这些资金存在。
但审计人员坚持要求,Wirecard通过将4亿欧元转移到其在德国的一个账户,来证明能控制这些资金。当Wirecard未能执行转账时,审计人员直接联系了菲律宾银行。两家银行都回复说,Wirecard的账户不存在。
几天后,布劳恩被要求公布审计结果。Wirecard的股价暴跌了80%,公司很快被迫破产。

法赫米·奎迪尔的卖空交易净赚了数千万美元。几家规模较大的基金赚了数亿美元。其他卖空者没有赚到钱,因为他们做空得太早了。
伦敦的基金经理利奥·佩里告诉麦克鲁姆:“我们一直低估了人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能力。”
在德国,有很多人辞职或被解雇: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局长菲利克斯•赫费尔德;德国审计监管机构负责人;其他欧洲银行的几位Wirecard首席分析师。
德国议会的一项调查举行了100场证人听证会,审查了近40万页的文件,得出的结论是,Wirecard及其支持者的行为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金融丑闻”。
报告指责了“集体监管的失败”,“对领先数字国家的渴望”,以及“德国人对非德国人的心态”——具体来说,是他们对奎迪尔和麦克鲁姆的态度。
报告总结道:“德国监管机构不适合‘互联网时代’”。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的主管、默克尔政府的财政部长奥拉夫•肖尔茨在议会调查中表示,他对自己任内发生的事情不负有直接责任。同年晚些时候,他成为了德国总理。
马库斯·布劳恩在慕尼黑被捕,并被控欺诈。他坚持认为,他是马萨利克等人精心策划的阴谋的不知情受害者。审判仍在进行中。Wirecard迪拜假合伙业务的负责人奥利弗·贝伦豪斯最近作证称,公司在亚洲的合作“从一开始就是假的”。
《商报》财经记者费利克斯·霍尔特曼告诉我:“如果你只把Wirecard理解为欺诈,你就无法理解Wirecard。这不是波将金村(注:专门用来给人虚假印象的建设和举措),也不是伯尼·麦道夫案。”
霍尔特曼还写了一本关于这家公司的书,他说,马萨利克经常“利用他的权力,推翻Wirecard非常非常小的合规部门”,向欧洲金融黑名单上的俄罗斯寡头发放银行账户、信用卡和借记卡。
他说:“德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欧洲的洗钱沙龙,只是最大的洗钱机器坏了。”
——————–
在过去的两年里,记者、检察官、警察和情报机构的调查,发现了一系列关于马萨利克在Wirecard之外的活动的惊人事实。在他位于俄罗斯领事馆附近的秘密豪宅里,他经常与政府官员和间谍举行聚会。他们来自俄罗斯、奥地利和以色列,但他似乎从来没有任何官方身份。
马萨利克也涉足政治事务。奥地利2017年大选前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东的移民。与奥地利极右翼成员有联系的马萨利克开始制定计划,在利比亚南部组建一支1.5万人的民兵组织,以阻止移民抵达地中海海岸。
组织会议在慕尼黑的豪宅举行,奥地利国防部和内政部现任和前任高级官员都参加了会议。此项目的安全顾问是俄罗斯前中校、政治经济学教授安德烈·丘普里金,西方情报界普遍怀疑他与俄罗斯军事情报机构GRU保持着密切关系。
丘普里金否认与俄罗斯情报机构有联系,他告诉金融时报,他只就“不断变化的政治和部落情况”向马萨利克提供建议。
在某个时刻,马萨利克要求一位名叫埃吉斯托·奥特的奥地利情报官员,在豪宅里设计一个防监视的房间。一名独立安全专业人士后来作证说:“这完全是一团糟,执行非常差。”
但奥特在其他方面也很有用。
根据泄露的数千页奥地利调查文件,在他的前上司马丁·魏斯的指导下,他代表马萨利克定期进行背景调查。魏斯曾是奥地利情报机构BVT的行动负责人。
据称,马萨利克花钱搜查了至少25人,他怀疑这些人与情报机构有联系。两人都没有进入BVT系统的权限,魏斯已经辞职,而涉嫌向俄罗斯出售国家机密的奥特已被重新分配到奥地利警察学院工作。但他们还是设法进行了搜索。(记者无法联系到魏斯请其置评。奥特否认进行过背景调查。)
目前尚不清楚马萨利克的目的。他似乎抓住每一个机会在政治事务中发挥作用,不管多么奇怪或徒劳。为了与特朗普的政策保持一致,他一度参与了将奥地利驻以色列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的努力。
马萨利克的名字出现在一家公司可能的种子投资者名单上,公司将收购剑桥分析公司的剩余资产,这家数据收集公司因影响选举而陷入丑闻。
当谈到利比亚事务时,马萨利克似乎很兴奋地告诉人们,他有可怕的战场暴力的随身摄像机视频,说这些视频显示“男孩们”在杀害囚犯。他夸口说佩特林斯基带他去了叙利亚,和俄罗斯士兵一起兜风去了古城巴尔米拉。据魏斯说,马萨利克“想成为一名特工”。但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他是特工。
然而,马萨利克在Wirecard的职位,使他能够接触到外国情报机构可能感兴趣的材料。2013年,公司开始向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发放假名信用卡,用于秘密调查,这意味着马萨利克可能已经了解了此机构的运营支出。
后来有消息称,德国的外国情报机构联邦情报局也使用Wirecard信用卡。马萨利克逃跑后,此机构声称不知道他与俄罗斯情报机构有联系。
2014年,马萨利克领导Wirecard与瑞士和黎巴嫩的私人银行合作,发行匿名借记卡,每年可预装高达200万欧元。在推销过程中,他对万事达卡表示,这种信用卡可以让超高净值个人免去被询问股票建议的烦恼,比如,当服务员拿到信用卡,知道了客户的名字时。
但是对于秘密行动费用来说,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有用的设置了。这是一种人人都能接受的匿名资产,非常适合贿赂政客、支付暗杀者或跨境转移大笔现金。
——————–
扬·马萨利克的逃跑飞机降落在明斯克。根据调查机构档案中心的说法,他从那里用假护照继续前往莫斯科,很可能是在佩特林斯基的协助下。两人都已改名;佩特林斯基下落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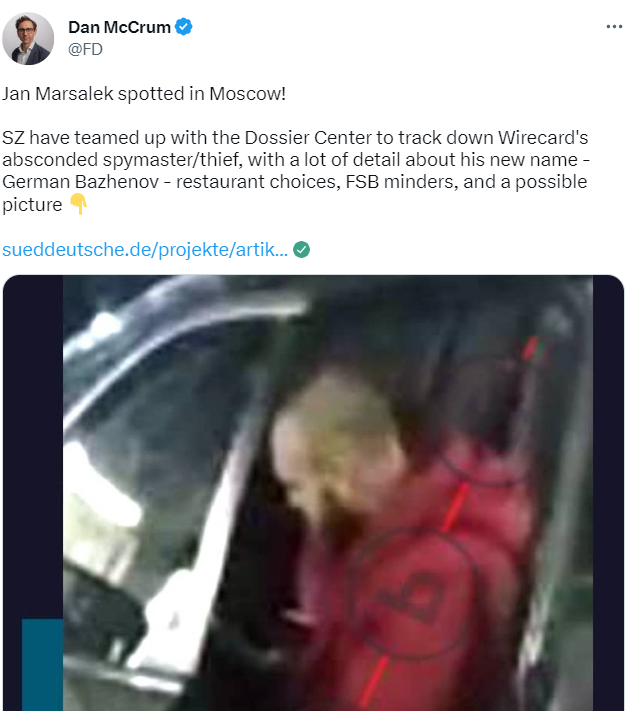
第二个月,德国向俄罗斯执法机构发出引渡马萨利克的请求。他们回答说,他们没有马萨利克的地址,也没有他入境的记录。他最后一次通话记录是去年。
私家侦探乔恩告诉我:“很明显,他藏在某个地方,只是因为旅行时各种系统的运作方式,每次他用护照进入另一个国家时,我们都能在这里得到这些记录。”
他推测,马萨利克很快就会“耗尽所有的钱”,并回忆起那些“人间蒸发”的客户,他们逃到俄罗斯,几年后回来时身无分文。
乔恩说:“在外面,你得为自己的安全买单。一旦你没有钱,你就会被抛弃。”
去年夏天,一张模糊的照片似乎显示,马萨利克在莫斯科的一个高档社区,穿着红色普拉达夹克,钻进一辆SUV。
利比亚前间谍主管拉米·埃尔奥贝迪在推特上写道:“这看起来确实像他。不过据我对他的了解,他从来不穿普拉达,除非俄罗斯人让他这么穿的。他喜欢布里奥尼(奢华男装品牌),和我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