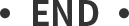Photograph:Sam Kaplan; prop styling: Brian Byrne

《大西洋》杂志2019年12月号封面。
美国是如何终结的
约尼·阿佩尔鲍姆(Yoni Appelbaum)
民主有赖于败选者的同意。二十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中,美国的政党和候选人加入竞选行列时是这样理解胜败的:败选既非始终如此,亦非不可接受。
败选者可以接受败选结果,调整竞选主张和结盟策略,在下一次选举中再接再厉。竞选中的主张和政策会遭到驳斥,有时是恶毒地驳斥,但不论言辞多么激烈,败选通常不会被等同于政治毁灭。人们从竞选中可能感受到高风险,但那绝少关乎生死存亡。
但近年来,事情发生了变化,这变化始自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并在随后愈演愈烈,
“我们激进的民主党对手受到仇恨、偏见和愤怒的驱使”,6月,特朗普在奥兰多启动谋求连任的竞选活动时这样告诉参加活动的人群。“他们想毁掉你们,毁掉我们熟悉的这个国家。”总统说服其支持者的关键在于:他,就是横亘于他们和深渊之间的那个人。
10月,弹劾的凶相隐隐浮现,他在推特上大发雷霆:“目前正在进行的不是弹劾,是政变,意在拿走人民的权力,他们的投票权,他们的自由,他们的宪法第二修正案、宗教、军队、边境墙,和上帝赐予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的权利!”他还引用了一位支持者的黑暗预言,即弹劾“将在这个国家导致一场如同南北战争那样的分裂,我们的国家绝无法从中恢复原状”。
特朗普末日启示般的鼓噪与这个时代的主题相得益彰。身体政治较近来人们记忆中的任何时刻都更加爆裂不安。过往25年间,共和党把持的红色地区和民主党把持的蓝色地区都变得越来越色彩鲜明,同时,民主党人向城市和城郊聚集,共和党人则布满乡村和远郊地区。在国会,那些隔开座位的通道已经变成裂痕,但两党在意识形态上原本存在共识。
随着两党铁杆信徒在居住位置和意识形态上渐行渐远,他们变得越来越敌视彼此。1960年,不到5%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表示,假如他们的子女与来自另一党的人士成婚,他们会不高兴;今天,据公共宗教研究所(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与《大西洋》杂志近期合作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35%的共和党人和45%的民主党人会不高兴,这这高于对不同种族和宗教人士通婚持反对立场的人士所占比例。
随着敌对情绪不断攀升,美国人对政治机构的信任程度以及彼此之间的信任程度在下降。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7月发布的一项研究发现,受调查者中,仅有一半人认为,不论谁赢得选举,他们的同胞都将接受选举结果。在一些外围地带,怀疑情绪变成了离心倾向:德州的右翼活动人士和加州的左翼活动人士已恢复有关脱离联邦的讨论。
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和其他机构的政治学者近期的研究发现,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乐于令人极度不安地贬低对方的人格。研究人员发现:“两党的铁杆信徒都乐意赤裸裸地称对方就像是动物,缺乏基本的人类品质。”总统鼓动并利用了这样的不安。越界是危险的。研究人员写道:“道德约束通常会防止我们伤害其他人,而非人格化的贬低则可能令我们放松对自己的这种约束。”[范德比尔特大学,创立于1873年,位于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是一所研究型私立大学,由美国铁路大亨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1794–1877)捐建。——译注]
相较于党派分裂的其他时期,包括1960年代晚期在内,直截了当的政治暴力依旧更为罕见。但过度狂热的鼓噪已在助长一些个人的激进化。
塞萨尔·萨耶克(Cesar Sayoc)因向多位知名共和党人投寄管状炸弹而被捕,他是福克斯新闻网的热心观众。法庭文件显示,他的律师称,他从特朗普的白人至上主义言论中获得了启示。法庭文件写道:“要将政治氛围和(萨耶克的)精神疾病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在一处棒球训练场枪击数位共和党议员(并重伤众议员史蒂夫·斯卡利斯[Steve Scalise])的詹姆斯·霍奇金森(James Hodgkinson),是脸书群组“终结共和党”(Terminate the Republican Party)和“通往地狱之路上铺满了共和党人”(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Republicans)的成员。
在其他例子中,政治抗议活动变成了暴力活动,这方面最出名的事端发生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Charlottesville),在那里,一场名为“将右派团结起来”(Unite theRight)的集会活动导致一名年轻女性遇害身亡。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Portland)和其他地方,左翼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运动(Antifa)与警方发生了冲突。
极端组织的暴力行径为一些理论家提供了火力,他们在想方设法煽动对另一方的不安情绪。
即将到来的人口巨变
如此深仇大恨从何而来?全球化的、后工业时代经济的压力。日渐加剧的经济不平等。社交媒体言过其实的夸张力量。居住地理位置方面的筛选。总统本人极具蛊惑性的挑拨煽动。如同在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中那样,每一个嫌疑人都参与到了犯罪之中。
但最重大的驱动因素可能是人口形势方面的变化。美国正在经历的转变,或许是任何富裕而稳定的民主国家都不曾经历过的:历史上主导美国的那个群体正变为政治上的少数派,而那些少数派群体则正在伸张他们的同等权利和利益。假如这一转变有过先例,那么那些先例就发生在美国这里:白种英格兰人起初占据压倒性优势,自那之后,这一占据主导地位的群体所掌控的疆界就一直在经历谈判。但那些先例几乎无法令人欣慰。很多再度发起的谈判引发了政治冲突或者公开的暴力,而几乎没有什么冲突和暴力有如同今天正在展开的那些冲突和暴力那般,来得意义深远。
在绝大多数美国人鲜活的记忆中,白人基督徒占了美国居民的多数。那不再是事实,且选民并非感受不到变化:将近三分之一的保守派人士和超过一半的白人福音派人士表示,他们因自己的信仰而蒙受了“很多”歧视。
但较这一已经发生的变化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即将到来的变化:再过四分之一世纪左右,非白人将成为美国的多数族群,具体时间点有赖于移民比例和族群和种族方面难以预料的变化。
那样的变化对一些美国人来讲值得庆祝,但对其他美国人而言则或可忽略。但如此转捩已在政治领域引发强烈反应,总统利用且恶化了这样的变化。2016年,表示对白人的歧视是一个严重问题,或者觉得在自己的国家就像是陌生人的白人工人阶层选民投票给特朗普的可能性,较不那么认为的选民几乎高出一倍。三分之二的特朗普选民同意,“2016年总统选举代表结束美国衰退的最后机会”。他们认为,特朗普是捍卫美国的代言人。
政治学者鲁伊·泰克西拉(Ruy Teixeira)和记者约翰·朱迪斯(John Judis)2012年出版的著作《崛起中的民主党多数》(The Emerging Democratic Majority)认为,美国的褐化,以及越来越多的女性、专业人士和年轻人转变为民主党人,人口形势方面的这些变化很快会将美国带入一个“新的进步主义时代”,共和党人在这个时代会遭到贬低,沦为永远的政治少数派。该书多少带着旗开得胜的兴味认定,民主党多数的崛起势不可挡,无可避免。
2012年奥巴马再度当选总统后,泰克西拉再接再厉,于《大西洋》杂志撰文指出:“民主党多数可能在美国出现并扎根。”
两年后的2014年,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遭受重创,朱迪斯随后的立场有所后退。他表示,崛起中的民主党多数已经成了海市蜃楼,而在白人工人阶层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共和党,这将赋予共和党人以长期优势。2016年的总统选举似乎证实了这一点。
但眼下,审视人口趋势后,很多保守派人士认为,泰克西拉没有错,只是结论仓促了。他们可以看出共和党在更年轻选民那里的时运愈发不济,并感受到那种反对他们的文化,那种文化谴责他们今天的一些看法仅仅是昨天的陈词滥调。他们正在失去未来可赢得选举的信心。诸多凶险的可能随之而来。
走向死胡同的共和党
共和党更多将特朗普的任期视作一种过渡,而非复兴,是一次短暂的休整,可用来减缓其衰落。这个大佬党没有只是在选举中展开争夺,反而加倍努力,缩小选民规模,提高其以选民中的少数赢得立法机构多数席位的几率。
2013年,最高法院的保守派法官废除了《选举权法》(Voting Rights Act)中一项关键条款,之后的头五年间,在这部法律先前加以约束的郡中,有39%的削减了投票站的数量。虽然不公正划分选区是两党共同的罪过,但在过去十年间,共和党人更加沉溺于此事。去年在威斯康星州,民主党人在州立法机构选举中赢得了53%的选票,但只赢得了36%的席位。在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人试图弹劾几位州最高法院的法官,因为他们曾瓦解共和党人重新划分该州国会选区的企图。特朗普行政分支曾试图限制在2020年人口普查中将移民计算在内,以削弱他们的投票权。
所有政党都动用手段以获得有力地位,但只有认为自己无法赢得大量公众选票的政党才会想方设法完全阻止他们投票。
美国历史中随处可见这样的例子:一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团体调整自身,适应了一些先前处在边缘地位的人口的兴起,这种调整时而是温文尔雅的,更常见的情形是愤愤不平,间或是暴力的。美国的党派联盟一直在重组,围绕新的核心重新站队。信仰、族群和阶级的疆界一度一成不变,但往往最终呈现出可塑性。一些议题赢得关注,或是隐没到无关宏旨的境地;昨日的对手成了明天的盟友。
但有时,这一重组过程会发生失败。政治右派非但未能伸出手来延揽新的盟友加入其同盟,反而变得僵化顽固,转而反对他们惧怕会将他们纳入其中的那一民主进程。一种由理念诠释的保守主义能够坚守自己的立场,抗拒进步主义,赢得皈依者宗奉其原理,并应时而变。一种由身份诠释的保守主义则将复杂的政治算计化约为简单的算法问题,且在某一时刻,那些数字不再增加。

Photograph: SamKaplan; prop styling: Brian Byrne
特朗普率领他的共和党走向了这个死胡同。假定弹劾未能将他赶下台,这种局面大有可能让他付出连任失败的代价。但总统的失败可能仅仅会加剧刺激他崛起的那种绝望之感,证明他的支持者的担心,即人口趋势已经不利于他们。那样的担心是美国民主所遭遇的最严重危险,没有之一;那是一种已在摧毁先例、敉平规则、拆除围栏的力量。当一个以传统方式运用权力的团体开始认为其黯然退场是无可避免的,认为其所珍重的一切的毁灭随之而来,它将不计代价,舍身一搏,保住它所拥有的。
政治学者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研究过东欧和拉丁美洲艰难推进的民主,他认为,为了生存,民主机制“必须在利益和价值观竞争中为所有相关政治力量提供偶尔致胜的机会”。但他补充说,这些机制还必须完成其他同等要紧的事:“它们必须使得哪怕是民主制度下的失败,也显得较非民主结局之下的某个未来更具魅力。”尽管目前把持着白宫、参议院和很多州的政府,保守派仍在丧失能在未来赢得选举的信心,对美国民主的平稳运转而言,这并非吉兆。他们认为选举方面的失利将摧毁他们,这甚至更令人忧心。
我们理当慎重,不能夸大危险。眼下不再是1860年的美国,甚至不是1850年的美国。但当一大部分美国人对他们既无法继续赢得选举又承受不起失败的代价这一点变得深信不疑时,就一个稳健的民主制度可能多么迅速地衰败下去,美国历史上的无数例证,尤其是那些来自南北战争前南方的例证,可以提供发人深省的讲述。
民主如何崩溃:20世纪的德国与19世纪的美国
共和党主流遭遇特朗普主义时的崩溃,是极特殊环境的产物,同时是其他事件令人不安的重现。
在其最近对西欧民主兴起的研究中,政治学者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专门探讨了一个决定性因素,可以区别实现了稳定民主的国家与那些掉入威权主义冲动陷阱之中的国家:核心变量与其说是政治左派的力量和品格,或急切争取更大范围民主化的那些势力的力量和品格,到不如说是中间右派的活力。一个强大的中右政党可以隔绝更极端的右翼运动,将攻击过政治体制本身的极端分子排斥在外。
左派绝无法免受威权主义冲动的影响。二十世纪最为残暴的一些放肆行径系由全能主义的左翼政权实施。但右翼政党一般来讲由一个社会内部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士组成,中间包括数量多到离谱的领袖,如商界富豪、军官、法官、州长,政府有赖于他们的忠诚和支持。齐布拉特认为,假如那些传统上享有特权地位的群体在一个更民主的社会中看到了有利于他们自身的未来,他们会认可这样一个未来。但假如“保守派势力认为,民主政治会将他们永远排斥在政府之外,他们就更有可能完全拒绝民主”。
1930年代的德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在二十世纪最具灾难性的崩溃,齐布拉特以之为例证明,民主的命运掌握在保守派人士手中。在中右派兴盛的国家,他们可以捍卫其支持者的利益,令更激进的势力丧失支持。在德国,中右政党摇摇欲坠,“并非它们的力量,毋宁说是它们的孱弱”成了民主走向崩溃的驱动力。
当然,民主国家在十九世纪最具灾难性的民主崩溃恰恰发生在美国这里;在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内部,对自身权力败落忧惧万分的白人选民的焦虑激发了那次崩溃。
在美利坚共和国的早期,蓄奴的南方掌握不成比例的政治权力。除了那两位姓亚当斯的总统,美国前十二位总统都蓄奴。前十六位国务卿中的十二位来自南方的蓄奴州。国会最初也由南方主导,因南方能将留作财产的受奴役人口的五分之三计算在内,用于分派众议员的数量。
共和国的早期政治是派系倾轧、戾气冲天的,受纵横交错的利益主导。但随着北方州正式放弃奴隶制,之后采取向西部扩张的战略,在那些颂扬自由劳动的州和那些财富与奴隶劳动直接相关的州之间,紧张局面在加剧,令地区冲突日渐凸显。到十九世纪中叶,人口形势显著有利于自由州,那里的人口增长迅速。横跨大西洋而来的移民不断涌现,他们在北方的工厂寻找工作机会,在中西部的农场中安家。到内战爆发前夕,生于外国的人口将占北方州人口的19%,但只占南方人口的4%。
作为美国政府中最民主的机构,众议院首先感受到这一新的动态,南方的应对是一致行动,将奴隶制议题排除在辩论之外。1836年,南方的众议员和他们的盟友在众议院强行推动言论限制令,禁止讨论哪怕是提到奴隶制的请愿,有效期九年。
如历史学家乔安妮·弗里曼(Joanne Freeman)在她的近著《血腥之地:国会暴力与通往内战之路》(The Field of Blood: Violence in Congress and the Road to Civil War)中所呈现的那样,华盛顿的奴隶州代表还诉诸恐吓、炫耀武器,要求与那些敢于非难这一特别制度的人士决斗,或者干脆在众议院的议员席用拳头和手杖攻击他们。1845年,俄亥俄州的约书亚·吉丁斯(Joshua Giddings)发表的废奴演讲令路易斯安那州的约翰·道森(John Dawson)极度不快,后者举起手枪,宣布他想杀掉其议员同事。其他议员——其中至少四人带着自己的手枪——赶紧冲向双方,局面一时僵持不下。那场面与其说是弗兰克·科波拉(Frank Capra)式的,不如说是赛尔乔·莱昂内(Sergio Leone)式的。到1850年代晚期,暴力胁迫相当普遍,乃至于议员进入众议院时通常会携带武器。(弗兰克·科波拉,生于1897年,卒于1991年,意大利电影导演,三度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赛尔乔·莱昂内,生于1929年,卒于1989年,意大利电影导演,代表作包括《黄金三镖客》、《美国往事》。——译注)
南方的政治家察觉到人口形势开始有利于北方,于是开始将民主制度本身当成一种威胁。南卡罗莱纳州参议员约翰·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1850年警告说,“在这个政府的每一个部门,北方都获得了决定性优势”,这是一种“专制”的局面,“不论结果多么具有压迫性”,南方的利益注定要被牺牲掉。考虑到众议院对他们不利,南方的政治家将重点放在了参议院,他们坚持要求,接纳任何一个自由州都应以新的奴隶州来平衡,以维持他们对参议院的控制。为守护他们的权力,他们将目光转向了最高法院:1850年代,最高法院有五位来自蓄奴州的大法官,占了多数。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他们的反击直指北方人制订他们自己社区规则的权利,开始将矛头直指州权。
但南方及其温言安抚的盟友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一种将南方种植园主和北方商人维系到一起的中右派共识,长久以来维持着合众国的完好无损。但随着人口形式不利于南方,南方的政治家开始放弃用他们的立场的道德正当性或妥协的实际案例去说服北方邻居的希望。他们没有寄望于通过选举民主捍卫他们的生活方式,反而动用联邦政府的高压力量迫使北方支持奴隶制度。他们坚称,任何向奴隶提供庇护的人士都应受到惩罚,甚至在自由州也是如此:1850年的《逃亡奴隶法》(The Fugitive Slave Act)要求北方执法官员逮捕那些逃离南方种植园的人士,并惩罚那些为他们提供庇护居所的公民。
在历时数十年的废奴运动失败的地方,南方的受迫害妄想取得了成功,制造出针对奴隶制度的敌意,而南方人惧怕这样的敌意。武装执法官拆散家庭,押送他们的邻居回到南方的奴隶制环境下,这样的画面将很多北方人从道德麻木状态唤醒。先前的数十年间,民主政治的推拉为南方制造出挫折,但南方放弃选举民主,转而支持反多数的政治。事实证明,这对南方的事业而言是灾难性的。
美国民主的维系有赖于中右派
今天,一个主要吸引了白人基督徒选民的共和党正在打一场失败的战斗。选举人团、最高法院、参议院或许可将失败延缓一段时间,但无法永远推迟失败。
共和党通过高压而非说服的手段维系权力的举措,说明了在一个多元民主社会中围绕一份共同的遗产而非价值观或者理念来诠释一个政党的极大危险。考虑一下特朗普的作为:他力推放缓移民到来的节奏,结果事与愿违,引发轩然大波,将公众舆论推向了他的限制性立场的对立面。在特朗普于2015年宣布参选总统之前,不到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应该增加合法移民的数量;今天,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应该吸收更多合法移民。不论特朗普独特的移民建议有多大正面意义,他都令那些建议更少可能获得通过。
对一个民粹主义者来讲,特朗普显然不受欢迎。但该事实不应令人安心。他越是刺激他的反对者反对他的议程,他就越是为他的支持者送去不安。左派的放肆行径更紧密地绑定了他的支持者和他;与此同时,右派的放肆行径令共和党更难以收获多数派的支持,这做实了这样一种不安,即共和党正在一个恶性循环中慢慢走向失势的境地。

Photograph: SamKaplan; prop styling: Brian Byrne
右派和整个国家可以退出这种局面,回归正途。我们的历史中随处可见一些显赫的团体,他们企图继续掌权时丢弃了对民主原则的承诺,之后在权力争夺战中失利,随后发现,他们可以在曾经极为畏惧的政治秩序中发展壮大。
联邦党人通过了《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Alien and Sedition Acts),用刑事手段打击批评他们的行政分支的意见;救赎时代的民主党人剥夺了黑人选民的选举权;持进步主义立场的共和党人从外来选民那里夺走了大都市的治理权。每一方都拒绝大众民主,他们担心他们会在投票中失利,惧怕随后可能发生的事情。在每个例子中,民主最终都被接受,没有在失败者那里造成悲剧性后果。此等美国制度发挥作用的时刻往往多于失灵的时刻。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一些年提供了另一个例子。蜂拥而来的移民,尤其是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移民,令很多白人新教徒感受到了威胁。美国颁行了禁酒令,一定程度上是要规范这些新到人口的集体习惯;发动了帕尔默搜捕行动(Palmer Raids),围捕了数千名政治激进分子,并将数百人驱逐出境;见证了三K党作为一个全国性组织的复兴,其成员多达数百万人,其中数万人曾在华盛顿特区公开游行;并通过了新的移民法,关闭了移民前往美国的大门。
在总统伍德罗·约翰逊执政期间,民主党充当了这场本土主义反对运动的急先锋。威尔逊卸任后四年,民主党要在威尔逊的女婿和阿尔·史密斯(Al Smith)之间选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史密斯是一位拥有爱尔兰、德国和意大利血统的纽约天主教徒,他反对禁酒令,公开斥责私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确定总统候选人时陷入僵局,投票多达一百多轮,最终选定的总统候选人名不见经传。但在四年后的下一次候选人角逐中,史密斯胜出,挤走了民主党内的本土主义势力。他整合了新获得选举权的妇女和新兴工业城市的少数族群选民。
民主党人在1928年的总统竞选中失利,但在接下来的五次竞选中获胜,他们所经历的选举是美国政治史中的占据最多优势的竞选之一。民主党政治家后来发现,捍卫他们所珍视的东西的最有效方式不是拒斥移民于党外,而是邀请他们加入。
丹尼尔·齐布拉特的研究启示我们,今天的美国政治体制是否能维持下去而不是进一步分裂,或许有赖于中右派眼下做出的选择。假如中右派决定接受选举上的一些失败,随后谋求通过辩论和魅力收获支持者,那么共和党就能保持生机。如同威尔逊之后1920年代的民主党那样,其分裂将愈合,其前景将获得改善。民主将得以维持。但假如中右派审视人口统计方面的巨变,发现无法忍受选举失利的前景,并与特朗普主义和源自族裔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的极右派共进退,那么他们将注定只能赢得越来越少的选民青睐,并极可能再度经历我们历史上那些最丑陋的时期。
特朗普主义与美国民主的命运
在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2012年竞选失败后和2016年特朗普当选之前形成的两份文件展示了风险和选择所在。
罗姆尼在总统选举中遭遇惨烈失败,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随后认定,假如坚定贯彻其路线,它注定将面对政治流亡。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呼吁这个大佬党采取更多行动,以赢得“西班牙裔、亚裔和太平洋岛民、非洲裔美国人、印度裔美国人、土著人、女性和年轻人”的支持。该建议中带着几丝恐慌;那些群体占到了2012年投票总数的将近四分之三。该报告警告说:“除非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对解决这一问题报以严肃态度,否则我们将在未来的选举中败北。数据证明了这一点。”
但不只是这个大佬党内部的实用主义者感受到了这样的恐慌。在一份支持特朗普主义的最有影响力的右翼宣言中,保守派作家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于《克莱门特书评》(Claremont Review ofBooks)宣布,“2016年的总统选举是93号航班选举:控制好驾驶舱,否则你死定了”。他的绝望呐喊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人口统计分析略相呼应。他写道,“假如你们不曾留意的话,我们这一方自1988年以来一直处在失败当中”,断言“我们完全被暗算了”。他指责那种“第三世界人口无休无止的输入”,认为这早就将民主党人置于“即将获得永久胜利的境地,这样的胜利会让他们永远不必再假装尊重民主和宪政的细节”。
上一次总统选举中,共和党在这两大相互矛盾的愿景中做出了抉择。2012年之后的那份报告在意识形态上诠释了共和党,敦促其领导人接触新的群体,强调他们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并重建共和党,将这个党建设成为一个能在一场总统竞选中赢得多数选票的组织。相较而言,安东的文章则将共和党诠释为受到了美国日渐增进的多元性威胁的“一个民族、一种文明”的捍卫者。他严斥共和党拓宽其联盟的举措是一种卑贱的投降。假如共和党在下一次选举中失利,保守派将遭遇“矛头指向反对和异见的恶意迫害”。
安东和其他大约6300万美国人控制好了驾驶舱。一位没有担任过一天公职,公然展示对民主程序不屑一顾的候选人碾压了共和党的多位旗手。唐纳德·特朗普非但没有接触多元化的选民,反而加倍押注于共和党的核心支持者。他向他们承诺说,他将保护他们免受某种文化和政体的侵害,而他表示,那种文化和政体正在走向他们的对立面。
到特朗普的总统任期结束时,共和党将面对在他崛起之前所面对的同样选择,只是会愈发急迫。2013年,共和党领导人清楚看到了他们面前的进路,并敦促共和党人接触那些自身价值观符合这个大佬党的“理念、哲学和原则”的多元背景的选民。特朗普主义消解了保守派理念和原则的优先性,而以族裔民族主义取而代之。
偏好连续性,热爱传统和习俗,对剧烈的转变报以健康的怀疑,——美国政治传统中的这一保守主义脉络为这个国家提供了必要的压舱石。美国这片土地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同时维持着强大的连续性。前往美国的每一波移民都改变了美国的文化,但移民自身也接纳并因之维护了美国的核心传统。令神职人员大为沮丧的是,到达美国海岸的犹太人、天主教徒和穆斯林变得有一点各行其是,将权力从教士牧师那里转移到了会众那里。农民和劳工变得更能白手起家。很多新来的人口变得更富于平等精神。所有人都变得更美国。
但美国的精英接纳了这些移民,并要求他们认同美国的建国理念,由此避免了被取而代之。这个国家的主流文化不断重新诠释自身,拓展边界,维持住了变动的人口中多数的支持。
美国开始形成之际,绝大多数美国人是白人、新教徒和英格兰人。但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之间那种根深蒂固的差别很快就变得几乎无法察觉。事实证明,白色自身是有弹性的,先是排除了犹太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随后又延展出去,将他们囊括在内。已经建成的教堂向形形色色的新教派别让出了位置,其他宗教信仰的扩散则使得“基督徒”成为紧密凝聚的一类人;那也壮大为犹太–基督教传统。假如美国的白人基督徒多数不存在了,那么某个新的多数群体已在显山露水,要取而代之。这是理解什么属于美国主流的某种崭新的、更恢弘的方式。
如是美国理念的魅力极其强大,乃至于感染到了甚至是异见人士。塞尼卡福尔斯(Seneca Falls)那些支持女性参政的人士、林肯纪念堂上台阶上的小马丁·路德·金和旧金山市政厅前的哈维·米尔克(Harvey Milk)都引用过《独立宣言》。美国拥有强大的激进传统,但其最成功的社会运动往往采用保守主义的语言,将它们的改革诉求说成是在表达而非拒斥美国的建国理念。(塞尼卡福尔斯,是位于纽约州的一个镇。1848年7月19日至20日,大约三百人在这里开会,讨论女性的社会、公民和宗教状况及权利。哈维·米尔克,生于1930年,卒于 1978年,加州政治家,曾任旧金山监事会成员,是首位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的加州当选官员。——译注)
即便是在今天,大量保守派人士依旧保持着信念的勇气,相信他们的事业能够赢得新的支持者。他们没有对在选举中获胜感到绝望,并且不准备抛弃道德说服,转而青睐强制手段。他们正在战斗,要从一位总统手中找回他们的党,这位总统的成功有赖于说服选民相信,这个国家正与他们渐行渐远。
对右派而言,这场战斗的风险远远高于下一次选举。假如共和党选民无法被说服,民主选举将继续为他们提供切实可行的制胜路径,他们可以在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内部兴旺发达,哪怕选举失利他们的基本权利也将受到保护,那么,特朗普主义就将继续得以延续到特朗普离任之后很久,并且我们的民主将因此而蒙难。
(作者是美国《大西洋》杂志高级编辑。本文原题“How America Ends”,原刊于《大西洋》杂志2019年12月号,是当期封面专题“How to Stop a Civil War”中的一篇。译者听桥,不保证准确理解,小标题是译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