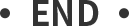编注:全文约5000字,非常详细的描写了当美国疫情暴发之时,纽约处在疫情中心的一家医院是如何在各种困难之下坚持工作的,是纽约时报一篇非常感人的优秀特写。
“他们穿上制服,然后出现在现场。他们就是这么做的,当然他们有焦虑,当然他们有恐惧,医生护士也是人。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如何,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会生病。但迄今为止,他们没有一个人玩忽职守,没有一个人不履行自己的使命。

甚至还没有到早上9点,德苏扎医生的绿色N95口罩已经歪斜了,口罩本来可以密封住她的脸的。
周一,在冰冷的雨中,她在布鲁克林医院中心的急诊科和外面的帐篷之间艰难跋涉,密切关注实习医生、护士和其他工作人员,他们将在那天为近100名未预约的患者筛查冠状病毒。
就在几个星期前,这个地方还被用来缝针和打石膏,现在已经有十几个人有感染的迹象,他们正在等待评估结果。另外十几个躺在轮床上,一个排在另一个前面,就像纽约市的停车场一样。一名戴着呼吸机的男子正在重症监护病房里等待空余的位置。
就在医护人员把一名心脏病发作的患者送进医院的几分钟前,德苏扎医生指了指预留给严重紧急情况使用的病床,病床之间用新修建的隔离墙与疑似病例隔开。“这是我们的安全区,”她告诉记者。
然后她纠正说,“这被认为是安全的,到底是不是安全,真的没有办法知道。”
三周前病毒突然袭击了这家医院。德苏扎医生开始在一张纸上写下每一个潜在病例的细节,这份名单已经扩大到800多名患者,其中大多数是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看到的。
她和医院里的其他人已经为不断增长的感染病例做好了准备,取消大多数手术以降低检查量,为疑似感染病毒的病人指定一个x光室,寻找供应品,阻止大多数访客,重新安排护士担任新的角色,为社区开通一条热线。
这家拥有175年历史的医院正在扩大规模,在这里,沃尔特·惠特曼(美国著名诗人)带来了桃子和诗来安慰内战受伤者,而白宫首席顾问安东尼·福西(曾因一再纠正特朗普在科学上的无知而出名)如今是美国最著名的医生,也出生于此。
州长科莫已要求所有纽约医院都这样做。这座城市现在是美国爆发疫情的中心,据报道,截至周三晚间,已有超过2万人确诊感染,280人死亡。
布鲁克林医疗中心获得了治疗464名患者的许可,但通常只有容纳250至300名患者的工作人员和床位。如果需要的话,它计划将这一数字增加一半,但它可能不得不将其增加一倍。

“我每天都处在不同的恐惧之中,”德苏扎医生说。如果病人的数量以目前的速度增长,她担心到下周急救室就没有空间了。如果许多病人病入膏肓,需要生命支持设备,她担心不得不在救谁不救谁之间做出选择。
那天早上,帐篷里的医务人员第一次在安全距离上举起手臂,好像在握着手一样,然后祈祷,做出正确的决定,自己与患者都能受到保护。德苏扎博士计划使其成为传统。她说:“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祈祷,团结一致,互相鼓励,而不会因恐惧而瘫痪。”
分布在整栋楼里的超过40%的医院住院病,人被确诊或疑似感染了冠状病毒,超过三分之二的重症监护病人也被确诊或疑似感染了冠状病毒。截至周三,已有四人死亡,其中三人是周一以来死亡的。
据医院负责人说,有超过六名医院工作人员感染了这种病毒,可能是被一名患者感染的,这是该医院的第一例,这名患者因另一个医疗问题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后出现了症状。
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被隔离。最令人担忧的是,本周初,两名医院工作人员自己也在接受重症监护。一位员工说,感觉就像一场看不见的战争。
周一,在急诊室里,德苏扎医生觉得自己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一个病人咳嗽得很厉害,几乎说不出话来。这名年轻男子是他们自己的一名医生,31岁的范(明显是华人的名字)是口腔外科住院医生,此前没有任何健康问题,经检测呈病毒阳性。
他在家里隔离了整整一个星期,以为自己正在好转,但那天早上开始咳血。他正在等待胸部扫描。除了从事他的职业,他没有其他已知的风险因素。
作为一名外科医生和病人,范医生向全国人民传达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如何对抗大流行。这声音很短,在一阵阵咳嗽之间低声说:你就呆在家里吧。

医院对个人防护装备严加把守,因为捐赠的口罩和其他物资正在迅速消耗。在急救室里,忙碌的工作人员唐娜·莫斯利周围电话响个不停。“等等,我一次只能做一件事,”她对一名员工说。
很快,她在办公桌下弯下腰,在一个盒子里翻找,然后递给记者一套:一个N95口罩,可以过滤病毒;一个外科口罩,上面有一个塑料护罩,包装皱皱的,是急诊室医生的亲戚捐赠的;一种薄薄的蓝色长袍,覆盖着一个人的前胸和手臂,背部敞开;还有一双蓝色的靴子。
员工必须签署一份表格。每天只有一套。
这是一家独立医院。所以在大流行期间,该医院没有母公司可以提供额外的物资,也没有其他机构的网络可以共享资源,医院主要服务于低收入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它抵制了被其他大医院合并。
“作为一家独立医院,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控制我们的资源,并真正为社区做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其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加里·特里诺尼说。
上周,这家医院检测棉签的短缺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它请求得到更多检测棉签的呼吁也传到了联邦政府。
“我们处于灾难中心,”特里诺尼说。

急诊室的电话又响了。是住在这条街上的一个男人,提供手工制作的口罩。“你是卖还是捐?”德苏扎博士问道,是捐赠,她记下他的电话号码,向他道谢。
医院收到了一些礼物,包括手套、食物和一个棕色的瓶子,瓶子里装着一种神秘的液体,这种液体是当地一家手工除臭剂制造商配制的,据说可以用来给口罩消毒,现在还没有人敢用。
前一天晚上,一辆黑色运动型多用途车送来了一份更大的礼物,来自美国联邦战略国家储备中心的几箱冠状病毒测试工具,总共200套。周一早上,美国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的两名身穿鲜蓝色制服的官员前来监督他们的使用情况。
但有一个问题。试剂盒的检测结果将直接送到患者手中,而不是送到医院。德苏扎医生问公共卫生官员,这怎么可能行得通。
“我们无法预测病人的临床病程,”她说。如果有人正在使用呼吸管,“他们将无法通过电话得到他们的结果。”
医院领导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测试的盒子并没有打开。

根据当地卫生部门通过传真传达给医院实验室的新规定,医生只能对那些病情严重到需要住院治疗的病人进行检测。德苏扎医生打印出了修改后的检测方案,这是该医院最近几周收到的第八份检测方案。她走进急诊科,撕下旧的指南,把新指南钉在墙上。
几周前,医院能够将棉签送到该市的公共卫生实验室,该实验室在一天内就能收到检测结果。现在,棉签每天被快递员取走两次,送到加州的Quest实验室。一开始是两天,然后是四天,现在是一周。
“那真是要了我们的命,”医院总裁特里诺尼说。周三,该医院有65名患者在等待结果。他们每个人都必须被隔离在一个通常用于两个病人的房间里。
该州已经要求医院提出一项将床位容量增加50%的计划。特里诺尼找到了空间,但“我们没有床,真的没有床,我们没有员工。”
医院向该市的志愿医疗后备队发出了通知,招募医生、护士和呼吸治疗师。
还有其他重要的员工。玛里琳·亨特推着一辆推车,车上装着垃圾桶和生活用品,她在急救室的洗手间里停下来换纸巾。“我们在第一线,努力做到最好,”她说。“我们互相支持,”她补充说,“向上帝祈祷这不会造成太大伤害。”
病毒袭击后,55岁的德苏扎医生连续工作了三周。她的副手就是被隔离了一段时间的人之一。德苏扎出生于巴黎,是贝宁(非洲一个国家)一位外交官的女儿,在好几个国家长大,在格林堡的布鲁克林医院接受过培训。
“我的心在这里,”她说。
在大流行期间,她主动提出远离家人,但家人坚持让她晚上回家。当她回到家,她马上洗了澡,用热水洗了衣服。她睡在一间单独的房间里,与他丈夫、他们的成年儿子和他的女朋友保持距离。
她说:“我主要关心的是如何保证他们的安全。我认为每个医护人员都有同样的担忧。”

在户外测试帐篷里,50岁的卢西亚诺·马哈查脱掉了滑雪服。一名外科实习生把听诊器放在他的背上。“你的肺很干净。没有必要进行检测,”罗伯特·贾丁医生说。
他告诉马哈查先生,只要他的症状——咳嗽和疲劳——持续,就回家呆在那里。
马哈查先生的第一语言不是英语,他同意远离其他人,但他似乎误解了自己是否感染了病毒。他说:“我以为我被传染了,但是感谢上帝,一切都很好,我没有。”
“他可能带有病毒,”贾丁医生告诉记者,然后向他的同事打手势。“我们可能都有。我们每天都接触到那些“比其他人更容易被感染”的人。”
上周,医学院学生被告知不要再来医院,但像贾丁医生这样从医学院毕业不到一年的住院医生,在评估帐篷里是大多数。
外面开始下雨了,地板开始塌陷。“我们需要帮助。”德苏扎医生在给医院的工程师发信息说。
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拖着脚用助步车进了帐篷。他和其他人一起坐在帐篷门口,那些人戴着医院发放的口罩咳嗽。当他告诉登记员他是来做伤口护理治疗的时候,工作人员很吃惊,“你得离开这里,”他指示。

戴安娜·珀内尔发烧一周,呼吸急促,病情比帐篷里的大多数人都严重。她今年62岁,高血压使她更有可能患上冠状病毒并发症,她怀疑这是她从舞蹈老师那里感染的。她在凌晨1点拨打了纽约州冠状病毒热线,等了两个小时,睡着了,直到听到护士的声音才醒来。
珀内尔说,有人告诉她,医生会给她回电话,让她做检查,但从来没有人这么做。她说,她联系了附近的一位急救医生,但他的诊所已经关闭了。
在急诊室里,珀内尔和其他十几名无精打采的病人一起坐在前快速通道区的一把蓝色椅子上,其中一名病人没有带口罩,还在咳嗽。
当她接受x光检查时,她被安排在了为没有被怀疑感染冠状病毒的病人保留的一侧,“她不是病人,所以我们可以把她放在这个房间里,”一名工作人员说。
拍完x光后,住院二年级的辛哈医生询问了她的症状——发烧、干咳、极度疲劳。
“是的,是病毒,”医生说。

除了来自联邦储备仍未打开的试剂盒外,这家医院只剩下最后四份试剂盒,被保留给危重病人使用。辛哈让珀内尔走到角落里的水槽边,把唾液吐到一个通常用来采集尿液样本的杯子里。
卫生部不推荐这种冠状病毒检测方法,但没有别的办法。
由于珀内尔的生命体征稳定,胸部x光片也很清晰,她被送回家中,等待卫生部门的电话,如果检测结果呈阳性的话。“如果结果不是肯定的,你就不打电话了?””她问道。
辛哈医生说是的。“因为我们正在对数千人进行检测,现在只有检测呈阳性的人才会接到电话。”
德苏扎医生走过急诊科时,停下来与两名重症监护医生交谈。
“你们这儿有一位,”她告诉他们。在等待搬到楼上去的病人中,有一个用呼吸机呼吸的危重病人。
医生何塞·奥尔西尼告诉她,病房已经满了,“情况还会变得更糟。”

德苏扎医生担心这种可能性,因为有报道说意大利医生不再向老年人提供生命维持设备,或在超负荷运转的医院提供不充分的护理,这样的传说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中。“我在问自己,这是不是我们最终要面临的局面,”她在周三晚上说。
一些接受了筛查的患者回家后出现呼吸困难,需要使用呼吸机。“每天都变得越来越难。”
重症监护病房有18张病床,周三晚上又增加了6张。医院重症监护服务主任加斯佩里诺说,所有病房都已满了,约三分之二的病人被确诊或怀疑感染了冠状病毒。
他说,可以立即在外科重症监护室再安排八名医护人员,还可以在手术室、手术恢复区和另一层的前中级护理室再安排更多医护人员。
患有肺炎的冠状病毒患者通常需要使用呼吸机两到三周。“强度水平更高,”医学主席加斯佩里诺医生说。“比典型的流感患者更难以给氧。”
他说,到目前为止,尽管有几名年轻患者正在迅速好转,但仍没有需要呼吸机的冠状病毒患者恢复到足以不需要呼吸机的水平。

加斯佩里诺医生说,周日晚上,另一名患者出现了心脏骤停,他和他的团队努力让他起死回生。医院的四名冠状病毒患者已经死亡,其中一些患者的家人选择停止生命支持。
本周,医院清点了所有的呼吸机,包括手术中使用的麻醉机。总共找到61个。加斯佩里诺医生说:“我们正在考虑购买新的呼吸器。”“我们正在让两个病人共享同一个呼吸机,”
一些专家认为这是有风险和困难的。但是他说,他们需要尝试这个过程,以确保它能正常工作。
尽管加斯佩里诺医生希望避免出现最糟糕的情况,但他说,他和伦理委员会的负责人正计划根据已公布的建议,起草一份有关医院如何分配呼吸机的指南。
周二,在奎斯特医院采购的120个棉签到达之后,医院负责对外事务的高级副院长伦尼·辛格尔塔利把联邦政府的检测棉签还给了该市的急救管理部门,半开玩笑地问能否把它们换成呼吸机。
第二天,他说医院接收到了圣乔治大学急救管理办公室和综合设备管理公司的12个呼吸器。
目前,工作人员仍在努力做一切可能的事情。“医院不能对其他病人关才,”在附近长大的辛格莱利说。
该医疗中心照顾儿童、孕妇、中风患者等。“你不能仅仅为了治疗冠状病毒而关闭医院,”他说。
工作人员继续他们的工作。
“他们只是把勇气藏在内心,”德苏扎医生这样评价她的团队。“他们穿上制服,然后出现在现场。他们就是这么做的,当然他们有焦虑,当然他们有恐惧,医生护士也是人。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如何,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会生病。但迄今为止,他们没有一个人玩忽职守,没有一个人不履行自己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