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formation-Justice|信 息 正 义

我不想在节目中显得悲观无力,
但我要说:
如果现在不能阻止川普,
以后会更糟。
——埃兹拉·克莱因
我不断告诉自己“当埃兹拉惊慌时,我也会惊慌”,“埃兹拉是如此冷静和理性,当埃兹拉失去这一点时,我就会知道事情真的很糟糕”……
今天似乎是这一天。
我们已身处绝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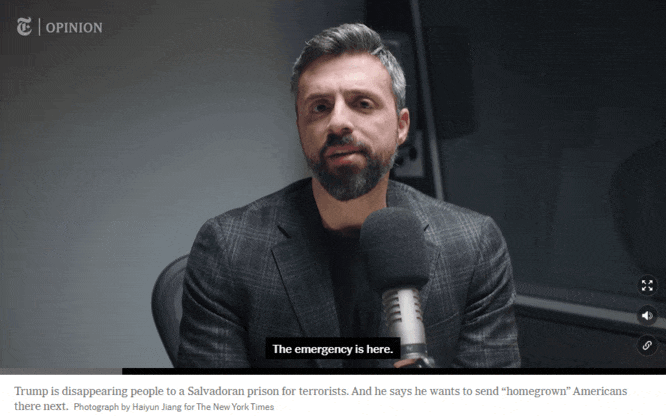
本文根据《纽约时报》播客《埃兹拉·克莱因秀》(The Ezra Klein Show)2025年4月17日播出内容的文字记录编译。播客主持人埃兹拉·克莱因(Ezra Klein)是美国知名记者、作家,曾创办了Vox Media。他主持的《埃兹拉·克莱因秀》影响力广泛,吸引知名学者、政界人士和行业领袖参与讨论,凭借理性、深入的对话风格,帮助听众理解复杂问题。它不仅塑造公共讨论,还影响政策思考,成为知识分子和决策者的重要信息来源。
【前言】
川普完全摘下面具
危机就在当下。不是半年后才发生。也不需等最高法院做出又一项裁决。现在就已发生。
也许对你还不是紧急状态。但对其他人是。他们是真实的人,有名有姓,我们知道他们的故事。
美国总统正在让人失踪——他们被押赴萨尔瓦多一所关押恐怖分子的监狱,监狱的缩写是CECOT。那是一座为将人失踪而建的监狱。里面没有教育、改造或娱乐,因为它根本不打算释放关押的人。用萨尔瓦多司法部长的话说,从这所监狱出去的唯一方式,是棺材。

4月14日,川普在椭圆办公室,坐在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布克尔(Nayib Bukele )旁边,对着摄像机,说他也想对美国公民这样做。
川普:如果是本土罪犯,我也没意见。我们正在研究法律。帕姆(PamBondi)正在研究。如果我们能做到,就太好了。我说的是有暴力倾向的人,我说的是真正的坏人。非常坏的人,和从外国来的一样坏的人。
川普告诉布克尔,需要再建五座这样的监狱,因为美国有太多他想送去的人。
川普:你觉得有特殊的一类人吗?他们和外国来的一样坏。我们也有坏人。我赞成,因为和萨尔瓦多总统合作,我们花钱少,还更安全。我们有很多犯人。我们有很多监狱,有私人监狱, 有些经营得好,有些经营得不好。

美国为什么需要萨尔瓦多的监狱?我们这里有监狱啊。但对川普政府来说,萨尔瓦多的监狱能逃避美国法律。
川普政府认为,他们送到萨尔瓦多的人都在美国法律管辖范围之外——他们不仅从我们的国家消失,还从我们的制度消失——从制度提供的任何保护或程序中消失。
在美国监狱里,律师和法庭能接触到囚犯,我们的仁慈能抵达囚犯。在萨尔瓦多则不能。
有很多人名。很多故事。让我告诉你其中一个名字,其中一个故事,尽我们所知。
基尔马·阿曼多·阿布雷戈·加西亚(Kilmar Armando Abrego Garcia)来自萨尔瓦多。他的母亲塞西莉亚在圣萨尔瓦多经营小吃店。当地一个帮派Barrio 18对其勒索,先要求每月付保护费,然后要求每周都付,威胁如果不付钱,就杀了基尔马的哥哥塞萨尔或强奸他们的姐妹。
后来,Barrio 18要求塞萨尔加入他们,家人就把塞萨尔送到美国。再后来,Barrio 18又要求阿布雷戈·加西亚加入,于是16岁的阿布雷戈·加西亚也被送到美国。
那大约是2011年。我们所说的非法入境是这样的:一个16岁的孩子因为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逃离了他唯一熟悉的家园。
阿布雷戈·加西亚在美国的生活很普通——也很不易。他住在马里兰,建筑业蓝领工人。他遇到一个女人,她叫詹妮弗,美国公民。她有两个孩子,一个患癫痫,另一个有自闭症。2019年,他们有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现在5岁,一只耳朵失聪,还有自闭症。
2019年珍妮弗怀孕时的一天,阿布雷戈·加西亚送孩子上学,把另一个孩子交给保姆,然后开车去Home Depot找活儿。他因游荡罪被捕,被问是否是帮派成员。
他予以否认。他被移民局拘留。
故事从这里开始变得离奇。阿布雷戈·加西亚被带走四小时后——而那似乎是他与美国警方的第一次接触——一名警探以秘密线人的身份指控阿布雷戈·加西亚是帮派成员。
阿布雷戈·加西亚没有犯罪记录——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萨尔瓦多。
他被指控加入了一个在纽约州活动的帮派,但他从未在纽约州居住过。提出指控的人从未接受交叉盘问。
阿布雷戈·加西亚的律师试图获得更多信息,但被告知,提出指控的警探已被停职,该部门的警官也不愿与他谈话。
阿布雷戈·加西亚的伴侣詹妮弗说,政府说因为他是MS-13黑帮成员而应被继续拘留时,她非常震惊。“基尔马不是,也从未是帮派成员。我敢肯定。”
2019年6月,阿布雷戈·加西亚被拘期间,他和詹妮弗举行了婚礼,两人隔着玻璃,通过警官交换戒指。同年晚些时候,法官裁定,因为阿布雷戈·加西亚可能会遭黑帮追杀,不能将其遣返萨尔瓦多——他的恐惧是可信的。阿布雷戈·加西亚被释放。
从那时起,他每年都到移民局报到。他做钣金工学徒,是工会会员,正在马里兰大学攻读职业许可证。他最后一次向移民局报到是今年1月2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阿布雷戈·加西亚对美国的任何人构成威胁。
但3月12 日,阿布雷戈·加西亚开车时被拦下,当时他5岁的孩子坐在后座。他被告其移民身份已改变。3月15日,不顾2019年法院的裁决,阿布雷戈·加西亚被押上飞机,遣送到萨尔瓦多,作为恐怖分子被关进CECOT。
川普政府在自己的法律文件中说,这是个“行政错误”。他们自己都说不该那么做——那是个错误。
这不仅是我的观点。我给你们读一下《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一篇社论,那可能是美国最著名的保守派杂志。这是第一句话:
关于基尔马·阿曼多·阿布雷戈·加西亚的法庭斗争极不寻常,因为没人否认政府在遣返他时违反了法律。
此案已提交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命令政府“为被关押在萨尔瓦多的阿布雷戈·加西亚获释提供便利,并确保此案依照假设他未被不当遣返的方式处理”。
我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描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这一切太怪诞了。
川普政府并不否认他们非法遣返了阿布雷戈·加西亚。他们否认的是,他们有权将其接回,说那个权力属于布克尔总统。但布克尔说,他也无法把他送回去。
你们不必信我的话。我还是引用《国家评论》:
这个借口很荒谬,因为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布克尔显然会遵从美国的任何要求。如果负责拉美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要求他在圣萨尔瓦多中心广场披着美国国旗骑独轮车,布克尔可能只会问是披早期的13州国旗,还是传统星条旗。
最起码,川普可以对萨尔瓦多征收他喜欢的关税。但美国在付钱给布克尔,让他关押阿布雷戈·加西亚等人。他那样做是顺从川普的意愿。他是川普的分包商。
川普和布克尔在白宫那次会面是完全摘下面具的时刻。
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恐怖之处,他说,很明显,川普和布克尔对此非常享受,两个人都声称对阿布雷戈·加西亚无能为力——没办法让他走法律程序;没办法让美国的法律系统履行职责,评估他是否是危险人物;没办法遵守最高法院的明确命令。
从他们的角度看,也许他们有道理。因为我认为最可怕的是,至少他们打的部分算盘是:顾及政治影响,他们不能释放阿布雷戈·加西亚,也不能释放不经正当程序遣送到CECOT的任何人。
因为如果他被释放,会发生什么?如果他回到美国,会发生什么?如果他能讲述自己的经历,会发生什么?如果——这是很可能的——他被川普的萨尔瓦多党羽酷刑折磨了[注],就不能让他向美国人民讲出来。
[注]4月18日,马里兰参议院Van Hollen被萨尔瓦多官方安排在一家宾馆见到了阿布雷戈·加西亚,后者谈及被绑架和单独监禁的精神创伤,但目前没有其关于在狱中遭身体虐待的报道。4月19日,最高法院下令暂停向萨尔瓦多遣送移民。
对川普政府来说,阿布雷戈·加西亚不是个错误,而是个负担,是个测试。测试他们是否有能力对任何人这样做,测试他们是否找到了他们认为的漏洞——如果能把人押上飞机,就能把他赶出我们的法律系统,把他扔进那种他们希望在美国拥有的古拉格集中营。
他们并不以此为耻。他们也不否认想对更多人这样做。
这就是独裁政权的运作方式。川普一直都清楚自己是谁,想要什么样的权力。现在,他正在运用那种权力。
而他身边的每个人——包括卢比奥(Marco Rubio)、帕姆·邦迪(Pam Bondi)、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和克里斯蒂·诺姆(Kristi Noem)——都在维护他行使这一权力的权利。
如果川普决定让你烂死在外国监狱里,那是他的权利。那你呢?你没有任何权利。
【延伸阅读】所有的美国人都不再安全

本届政府执政还不到百天,我们就已面临这种恐怖。我能感到自己内心深处有想逃避的欲望。而去面对这一切,太难,也太影响身心。
但是,川普已直截了当、公开地表明:他打算把他憎恨的人送进美国法律管辖之外的外国监狱。他不在乎——他甚至都不试图搜罗——那些人是否犯有他说的罪行。因为这无关于他们是否有罪,而是关于他的权力。
如果他能这么做,如果他想这么做,那除此之外,他还能做什么?还想要什么?如果为他服务的人愿意给他,愿意维护他这样做的权利,那他们还会给他什么别的?他们还会维护什么别的?
这就是紧急状态。不管你喜不喜欢,它已经降临。
我今天的嘉宾是阿莎·兰加帕(Asha Rangappa)。她是前联邦调查局(FBI)特工,现任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助理院长。她还是Substack时事通讯The Freedom Academy的作者。
—— 埃兹拉·克莱因

现在已是紧急状态
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编译作品。欢迎转载、分享、转发。
我们已正式陷入宪政危机
克莱因:欢迎来到节目。
我想从我们现在所处的黑暗时刻说起。在我看来,至少在阿布雷戈·加西亚案中,政府在直接违抗最高法院的命令。
法院或法律系统还有哪些应对手段?
兰加帕: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分析家都说,我们已正式陷入宪政危机。
通常的做法是以藐视法庭罪起诉政府,可以对具体官员处以罚款。你我这样的人被控藐视法庭的话,最终惩罚是坐牢。
我怀疑这最终会发生在本届政府任何人身上,虽然那也是在法院权力范围内。
克莱因:但川普可以赦免他们。
兰加帕:说到底,行政部门拥有执法权。川普控制所有执法机构,包括美国法警。
因此,即使打到最高法院,司法与行政对峙,我也不清楚到底能采取什么措施去执行法院命令,这就给川普政府留下一张川普牌(王牌)——这不是双关语。
克莱因:川普政府对该命令的解读是——不知道用“解读”这个词是否合适(斯蒂芬·米勒的话肯定是对该命令的歪曲)——这是他们的一个重大胜利,因为最高法院说,没有人可以强迫他们。他们也许必须提供便利,但不一定非要实施。这句话里有很多强行狡辩。
但他们认为,高院为行政部门和川普创造或确认了相当大的权力范围,那就是外交政策方面。
如果你读懂了,高院的意思是,他们对此什么都不会做。
兰加帕:首先,斯蒂芬·米勒对高院判决的解读并不完全准确。高院虽然提到在外交事务上尊重行政部门,但明确支持下级法院要求政府为遣返提供便利的命令。
在与外国政府谈判和交涉方面,高院不能下令该怎么做,但说了政府需要竭尽所能,为这个人回到美国提供方便。
从大的方面来看,这是有意为之。无论是驱逐出境、取消签证,甚至关税,你都会听到这些关键词:外交事务、恐怖主义、国家安全、国家紧急状态。这些领域都是行政部门的核心权力,法院会给予高度尊重。
因此,他们用这些措辞来描述问题时,就划出一大片权力范围,基本上可不受监督地行使权力。
再加上法院去年做出的绝对豁免裁决(该裁决保护核心职能部门免于承担任何责任),只要政府行动足够迅速,就像在本案中那样,就有很大空间可以肆意行事而不受惩罚。
克莱因:所以只要总统说是为了国家安全,就意味着不违法?——效仿尼克松的老话。
兰加帕:[笑]我不会说这不违法,那只意味着他的意见会得到很大尊重。
例如,事实认定上会倾向于尊重他的判断。比如对美国处于国家紧急状态的事实认定。他的事实判断可以是我们被入侵,也可以是某人的行为侵犯了他的外交政策特权。
这些事情都有很大的自由度。迄今为止,所有这些情况下,行政部门都可以根据国会的授权自由裁量。因此,这些实际上是国会的权力,国会将之授予行政部门,初衷是,某些情况下,行政部门可能需要快速作出决策,以行使这种权力。
它假定总统会本着国家利益,恰当行事。
克莱因:我想先确保我理解你的意思,确认我内心的恐惧——你也说到恐惧感——是有理由的。
我听你的意思是,法院对此没有任何制约力。他们告诉行政部门要为阿布雷戈·加西亚的返回提供便利,并假设“行政错误”没发生过,允许他享有正当程序。
川普政府已明确表示他们不会那么做。你似乎不指望高院会进行第二轮裁决,以某种方式强迫他们做他们不想做的事。
兰加帕:我不知道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高院能强迫他做什么。如果川普说,我和布克尔谈过了,他说他不能归还。或者,如果川普耸耸肩说,他不会归还——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就是那么说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也无能为力。
有趣的是,从政策的大局来看,这对川普并没有益处。把阿布雷戈·加西亚接回来,在法律上符合他的利益,让他可以说:看,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能纠正错误。我们应该快速行动,把所有这些人抓起来,快速遣返,因为如果我们犯了错,可以把他们再接回来。
实际上,我认为那将是个更有力的辩词。但现在他关注的是权力角斗,是对司法的抵制。
因此,某种程度上,法律上的利益与政府的争权行为相矛盾。如果大家看清这样的举动无法挽回,错误无法纠正,那么或许会阻止他们继续驱逐出境。
克莱因:在一个平行世界里,这样做可能符合他们的法律利益。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阿布雷戈·加西亚很可能受了虐待或酷刑。让他回到美国,让人们听到他的经历,将对美国政府造成政治上的毁灭性打击。
因此,实际上,他回来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或者说,任何根据这一授权被遣返的人回来都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如果他们回来,人们会发现政府犯了可怕的错误,无缘无故把人发配到地狱,那政府就有动机不让人把这个事讲出来,让布克尔把他们永远关在CECOT。
兰加帕:对。我唯一想说的是,把人接回来会有坏处,但如果这是个一贯愿意遵守法庭命令的政府,他们还是会去做。
宪法黑洞
克莱因:小布什执政期间,曾有将被视为威胁的犯人转移、送到不受美国法律约束的暗黑之地监狱的臭名昭著的做法。
我们现在看到的理论和权力,与当时引用和使用的相似吗?
兰加帕:很相似。这更像是布什政府把人送到关塔那摩。
暗黑之地是有用的,是为了获得那些被拘者可能拥有的情报,根据美国法律,那些审讯方式是非法的。我不是为那种行为开脱,是说他们认为会得到有用的情报。
但就回避法院权力而言,布什政府的做法是,他们研究一些二战先例,那些先例称,敌方战斗人员如果被关押在不受美国控制的地方,就无权申请人身保护令。
布什政府说,嘿,太好了,我们可以把人关到关塔那摩,那里在古巴主权控制下,我们可以把那些人都关到那个好地方,法律管不到。
这导致了911后一个相当强大的判例。法院不喜欢被排除在考虑之外,所以做出决定,说:“不,我们有权查看你在那里干了什么”。
顺便说一句,那个判例造成的讽刺是,关塔那摩被拘者是在国外抓获的,从未踏上美国的土地,却有申请人身保护令、正当程序权、质疑其敌方战斗人员身份的能力,并受《日内瓦公约》保护。
而现在,那些在美国居住了十年的人却没有同样的特权和权利。
克莱因:太可怕了。
兰加帕:非常可怕。令人震惊的是,政府在法律上非常精明,研究过这一点的任何律师都了解布什政府的轨迹,他们知道:想让什么成为宪法黑洞, 就必须完全移到另一个国家。
不是为了获取情报。而是需要把他们关到那里,然后我们扔掉钥匙。
克莱因:他们在法律上很精明。川普政府在不同领域做的很多事都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他们想保护这种权力,并最大限度将其扩大,他们会谨慎地选择对象、案件、法律和当局。
而在阿布雷戈·加西亚案中——尽管不限于他——看到的是他们没那样做。无论是否有意为之——很难搞清是无能还是蓄意的恶意——他们选择对其做出那种事的人,会让政府很难看。
人们知道他的名字是有原因的。这起特殊案件之所以产生轰动,也是有原因的。当然,不管是否有意,他们做的决定是,如果他们能在这个问题上获胜,那他们的权力就能扩大。
如果他们不必仔细挑选送往布克尔的地狱的人,如果不必是绝对十恶不赦的罪犯,如果不必无懈可击地确认某人是大家不希望出现在美国的恐怖分子——而只需“川普这么说了”,那他们就拥有了将人失踪的权力。它不仅是一种国家安全权力,而是随时随地清除几乎任何人的能力。
他开始这样做,在受到批评的情况下,仍在白宫和布克尔一起,叫嚷说需要造更多的监狱,说也许下一个就是本土的。你怎么看?美国公民是特殊人群吗?那我们好像进入了完全不同的世界。
无论他们是否精通法律,这都不是他们精心挑选的测试案例。对于这个案例,高院已经告诉他们:你们不能这么做。
而他们的答复基本是:我们能。
兰加帕:好吧。我对你的话唯一改动是:不是“如果我们能在这件事上获胜,我们就能做所有事。”
而是“如果我们挑战成功,我们就稳操胜券了。”
克莱因:是的,我指的不是法律上的胜利,而是权力上的胜利。
兰加帕:没错。掌握权力。
这就是川普政府与布什政府之间的区别。
布什政府不希望最高法院对一些最终不利于他们的事情做出裁决。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很好的法律依据时,就会将被关押者转移出去,或让他们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避免问题得到真正的回答。那样,他们的行为就仍处于某种灰色地带。
正如你提到的,川普政府愿意就这些糟糕的案件被诉。糟糕的案件造就糟糕的法律,尤其是对行政部门而言,但他们并不在乎。我认为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因为这体现了无视法律的倾向——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
克莱因:本届政府执政还不到一百天。但如果让你从大局的角度告诉我,川普政府希望如何利用国家的安全和司法机构去实现其目标——无论目标是什么——你用什么框架进行理解?
兰加帕:我认为这只是权力的整合。这是在僭取国会权力——如我之前提到的,国会在自行让渡权力——现在他们又僭取司法权力。
实际上,川普政府在充当“准司法“机构。他们围捕民众,同时充当法官、陪审团和执法者。
他们说,相信我们,我们认定这个人有罪,这个人是恐怖分子,这个人犯了法。
因此,这是巩固权力。这是独裁行为。
他们发出挑战:谁能阻止我们?
如果他们行动够快,让人进入宪法黑洞,他们就赢了。
弹劾权力已然破碎
克莱因: 理论上讲,能阻止他们的权力在国会——如果国会愿意的话。
兰加帕:我认为,能以系统性方式阻止这一切的权力在于国会。
1798年的《外敌法》是对国会战争权力的授权。
克莱因:那是什么法?我们来说说吧。
兰加帕:《外敌法》于1798年在与法国的准战争期间通过,它允许总统在宣战或外国入侵期间清除14岁以上的外籍敌国人员。
法律初衷是,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效忠自己的国家,因此有人可能是间谍和破坏分子。为保护国家安全,行政部门需要有能力迅速清除那些人。
今年之前,它只被引用过三次:在1812年战争、一战和二战期间。二战中,人们得到单独听证,至少确认他们是否是敌国的公民。
但现在它被用到移民问题上。川普声称非法移民构成入侵。具体说,是黑帮Tren de Aragua的入侵。因此,加入这一帮派的14岁以上男性都适用《外敌法》,可以被驱逐出境。
克莱因:当你说这是政府诈称有权力时——我同意——是因为川普真的深信南美黑帮是对美国的威胁?还是说,这是更广泛的、从根本上说是独裁者的权力诈称——国家和领导人面临一系列敌人,于是他们动用一切可动用的权力去实施控制?
兰加帕:我认为是后者。不过我觉得他们在拿这个群体做测试。因为大多数人不会反对:有黑帮进入美国,他们是危险的黑帮,那让我们把这个战争概念用到这里。当然,Tren de Aragua是很危险的黑帮。MS-13也是。
他们的想法是,看看能做到什么程度不受惩罚,然后就可以得寸进尺,不断扩大这个群体的范围,使其类别越来越广。
川普已经在和布克尔讨论:嘿,为什么不把本土罪犯也加进去呢?
因此,我认为这是一种试探,看如何做到这一点。这是不经法律程序的立即遣返:怎样才能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把人遣返?
这就是他们的目标。然后,他们会把更多的人纳入敌人行列。
克莱因:当川普想把“土生土长的罪犯”送到萨尔瓦多时,他说:“我们得研究一下这方面的法律。”
这方面的法律是什么?
兰加帕:将美国公民送往国外的古拉格集中营,让其在那里“烂死”,是公然违反宪法的。有一项名为《不拘留法》的法律规定:除非根据国会法案,否则不得监禁或以其他方式拘留任何公民。
克莱因:但是,如果能以一个连自己都承认是行政错误的理由把人送去——
兰加帕:问题就在这里。如果只是把人赶走——那么游戏就结束了。如果他们能不让司法部门插手——那正是布什政府企图做的——如果你甚至都不能踏进司法这扇门,行政部门无需在把你押走前证明把你定为恐怖分子或敌人的理由——那么,我们绝对就是1973年的智利。然后,黑色面包车会在半夜出现,围捕你,你会失踪——
克莱因:你认为我们现在是了吗?
兰加帕:我认为我们还没到那一步。
克莱因:不是黑色面包车,而是1973年的智利。我们和那有什么不同?从你的描述中,我没发现能得到安慰的东西。
兰加帕:我知道。
克莱因:我并不是在向你索要什么可以安慰的东西。
我在这次访谈话的开场白中说:在我看来,紧急状态已经发生。
兰加帕:是的。
克莱因:我们面临考验。
兰加帕:是的。
克莱因:他们是否可以藐视法庭,执意去做?问题摆在这里。正视这个问题是很艰难的。
所以,如果你认为我们还不是1973的智利,那很好,我也宁愿不是。但如果你认为已经是了,那又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身处1973年智利的深渊,你该怎么办?
兰加帕:宪法对此有个补救措施,那就是弹劾。
这需要政治上有意愿。需要某种共识,即这是不可接受的,已超越界限;这是不符合宪法的:这个人在滥用权力,违背了自己的誓言,或违反了法律。
宪法危机是对司法部门的藐视,但同样重要的是,国会在这种情况下未能采取行动,不管是站出来收回一些授权,以阻止他把国家紧急状态滥用于其他领域,还是迈出最后一步说:这太出格了。
我认为现在已进入可弹劾范畴。这些都是可以弹劾的罪行。这是对权利的剥夺。
在我看来,川普和布克尔在搞剥夺人们权利的犯罪阴谋,达成的是犯罪协议。根据《宪法》或美国法律,以法律名义剥夺人们的权利是犯罪。
这正是他所说的他要做的事。我们知道,他不会因此承担刑事责任,因为他的行为是官方行为,而最高法院已经说过,这些行为超出国会的权限,不能定罪。
我们还剩下什么?
克莱因: 问题在于,在政党国家化、两极分化的时代,弹劾权力已然破碎。
兰加帕:如果我们不再有超越党派的共同价值观,那权力就是破碎的。
克莱因: 就是说,弹劾权力是个破碎的权力。[笑]
兰加帕:是,但补救措施只有这个。如果川普藐视法庭,法庭没有独立的执行机制。
克莱因:我不想让人彻底绝望。
兰加帕:我们现在是穿着睡裤、望着天花板发呆的状态。
完全不同的世界
克莱因:想象这样一个世界:我们在这些恐怖事件中熬过一两年,然后中期选举民主党大胜。
我一直说——半开玩笑地说——能拯救美国民主的,可能是川普对全球经济有着最愚蠢的的看法,他毁了401(k)、物价和小企业的进口能力,这给他的对手一个难以置信的中期选举机会。
因此,假设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拿下众议院——赢参议院不太可能,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他们还是无法弹劾,因为他们没有参议院多数,无法将其定罪。
但他们会突然有了很大权力。他们可以控制政府各领域的拨款,可以将很多政府成员绳之以藐视法庭罪。
突然间,我们不一定有能力结束川普,但有了巨大筹码。
我认为,这是成功的途径。
兰加帕:我很高兴你提到了拨款授权,因为在本案中,有一点仍不清楚,那就是遣返这些囚犯的钱是从哪里来的。那笔钱最初是做什么的?还有,那份协议的条款是什么?
法律上,有个名为《凯斯-扎布洛基法案》(Case-Zablocki Act)的规定,要求行政部门、国务卿向国会通报与外国达成的行政协议。因此,从技术上讲,他们必须披露,应该在国务院网站上公布。
对于你提到的扣留拨款,911期间,国会禁止拨款将关塔那摩囚犯转移到美国接受刑事法庭审判。因此,他们只能困在那里。
因此,在我看来,如果国会愿意,他们可以禁止拨款将人送往萨尔瓦多。
克莱因:他们还可以拿走很多川普政府想要的东西。
设想一下民主党控制两院这种不太可能发生的情况:民主党可以简单地以“阻挠议事”得到更多豁免。他们可以从川普手中夺走关税权;可以把关税权交还国会,而国会本来就是掌握关税权的。突然间,川普没有了他最喜欢的国际经济工具。
然后,一切都变成需要谈判。川普现在使用的大量权力都基于旧的法案,而那些立法不是为今天的情况制定的。
国会不喜欢回头重新审视那些不适合今天的旧的立法,因为他们很难就任何事情进行立法。没人因为回到过去,堵住旧的漏洞和权限而在政治上加分。但他们可以那样做。
在一个三权对峙的世界里,并不是要么弹劾,要么什么都不做,而是一切都可以用做筹码。
美国总统没有向其他国家征收关税的权力,而必须通过法律实施和完成。那是国会赋予的权力。
政府效率部(DOGE)所做的一切,他们在削减支出上做的事,都是国会赋予他们的权力。国会可以全部收回。
兰加帕:是的,当然。从更大的方面上说,要重新想象坐白宫的会是什么人。
水门事件后,我们进行了改革,因为突然间我们必须重新想象:总统要是越界,怎么办?
因此,我们有了《1978年政府道德法》,有了《独立顾问法》,有了对总统使用税务信息的限制,因为突然间,发生了那些例子。
坦率地说,我们早就知道这一点——这些事早该做了,钟摆早该摆动了。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不能授予行政部门这么大的权力。
这很难,因为你也不想束缚总统的手脚。如果总统需要,川普用来征收关税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实际上是个外科手术式的杠杆工具。我们希望总统在需要与特定的外国势力就特定紧急情况进行谈判时,能拥有这样的工具。
但正如你所说,我们已经不在那个世界里了。我们现在处于完全不同的世界,国会必须正视这一点。
克莱因:记得一位我很尊敬的政治学家在川普第一任期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一种政治制度的设计能在选出糟糕的人时依然良好运作。
根据“选出糟糕的人”这一理论来设计政治体制,会让体制难以驾驭。因为从本质上讲,你要束缚他们的手脚,因为他们很糟糕。
但是,如果把有独裁倾向的人选入一个假定总统在根本上心怀善意的系统,那就给动机邪恶的人以可怕的权力。
兰加帕:我想补充一点,现在情况已发生了变化。尼克松之前可能存在两大假设:A. 总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B. 如果有必要,国会愿意使用其终极武器,即弹劾。如果这两点都被排除在外,那就是个全新的格局。我们必须适应这一现实。
FBI可以很可怕
克莱因:我们一直在谈论我们知道的政府正在做的事情。
我想采访你的一个原因是,从一开始我就担心,我们不知道政府在做什么。
卡什·帕特尔(Kash Patel) 和丹·邦吉诺(Dan Bongino)被提名进入联邦调查局(FBI),一个你工作过的地方,我非常震惊。参议院共和党人居然赞同这一提名,让我感到恐惧。
我们看到这届政府在光天化日下如何运作,而FBI是个强有力的组织,其本质决定了它在暗处运作。目前管理它的人,唯一的资历是对川普忠心。
你对这些正在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事情看法如何?
兰加帕:很高兴你提到FBI在暗处运作。它的国家安全部分确实是在暗处。但调查的性质是,很多事情发生在上法庭之前。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FBI不是根据立法运作的。除了宪法,没有其它法律规定它如何使用调查权。
它受总检察长发布的《总检察长指南》管辖。这些准则规定启动调查前必须达到的标准,在不同调查中可以使用哪些手段,需要获得哪些批准,等等。
这些都可以在内部更改、取消或不遵守,而我们不会知道。
我们能做的是看看实际发生了什么,或没发生什么。例如,“信号门”(Signalgate)这种事件通常会由FBI进行调查。或者司法部、司法部长会任命一个特别顾问进行调查。加兰(Merrick Garland)在拜登持有或不当处理机密文件上就是这么做的。
但这一次没有调查。最近有一项针对克雷布斯(Chris Krebs)的行政令,他是CISA的负责人,要求——
克莱因:能说一下CISA是什么吗?
兰加帕:CISA是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隶属于国土安全部,成立于2018年,负责监督选举安全。
克雷布斯是第一任局长,他公开宣称2020年大选是安全的,向人们保证,选举运作正常。这显然削弱了选举被操纵的说法。
川普命令司法部对克雷布斯进行调查,这告诉我——除非有我不知道的证据——《总检察长指南》已被丢进垃圾桶。我的意思是,他们遵循那些准则的话,就不可能进行毫无根据的调查。
一名负责俄罗斯调查的分析师被停职。帕特尔的书中提及这个人,是他的敌人名单上的。
因此,这告诉我,仅从外在的东西来看,FBI已不再是过去我曾工作过的机构。
这非常危险,因为FBI可以做很多事。
克莱因:我们来看看它能做些什么。
我对FBI的印象是,它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官僚机构,川普政府认为这个机构对他有敌意,并将其当作敌对的来对待。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对川普怀有敌意。那里会有些卡什·帕特尔认为忠心的人,一些想通过卡什·帕特尔在FBI晋升的人,还有他们想招进去的人。
因此,虽然FBI不会整个都变成他私人的整治仇敌的机构,但肯定会有几十、几百个人,可以成为特殊的团队,帮他那么干。
过去,在胡佛(J. Edgar Hoover)的领导下,FBI挖了很多人的信息,用来敲诈勒索,其中有名的包括马丁·路德·金。
因此,可以想象一些在我看来并不牵强的事情,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那就是:帕特尔和邦吉诺(Bongino)被任命担任这个职位,他们都是川普的忠实拥护者,他们明白自己的工作是为川普的意志服务,他们明白FBI和FBI内对川普忠实的特工是他们的工具。
这样一帮人能做什么?
兰加帕:他们能做很多事。从启动调查到进行某种司法检查,有很大的空间。
例如,他们可以对你进行人身监视——只作为一种恐吓手段。我们说到黑色面包车,对吧?他们可以把车停在你家门前,一直监视你。他们可以去问讯与你合作的人,大家却不清楚他们在调查什么,就会产生你很可疑的印象。他们可以翻你的垃圾桶,查你拨打的所有号码;他们可以拿到你的金融交易数据,找出你花钱的方式和地点。
这些事情他们都可以做,而且无需向法庭出示合理的理由。危险并不在于你会被指控莫须有的罪名,而是你其实永远不会被起诉。那将是胡佛式的行动,要么像你说的,偷偷收集信息,然后将其武器化,要么仅仅是骚扰和恐吓。或者让你付出高昂代价——你得请律师,因为你想搞清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有这些都可能发生。这也是制定《总检察长准则》的原因。
如果你仔细听过帕特尔和邦迪的确认听证会,他们当时说:我们会遵守法律。
对他们来说,法律就是宪法第二条,即单一行政理论。那种观点认为,如果总统这么做了,那就是合法的——不管在执法方面,还是在确保法律得到忠实执行方面。
所以,没有保护栏。根据他们对法律的解释,总统的意志就是他们接收的命令。
克莱因:根据他们对法律的解释,告诉纽约南区的职业检察官不要再找亚当斯(Eric Adams)市长的麻烦是合法的,因为他已经和川普达成了某种协议。
尽管说法不一,但显然他与川普政府达成了协议,他按政府说的去做,以换取保护。
这是在邦迪担任司法部长期间发生的事情。
对我来说,这是所有一切的重要信号。它发生在光天化日。那些检察官公开辞职后,政府仍一意孤行,制造了大量关于他们的负面新闻和宣传。
我认为,川普的世界观及如何在其中运作的关键在于筹码。他对国家、人民和商业伙伴都提出要求,他会在一切领域想方设法得到筹码。
关税是筹码。权力和初选也是筹码。
兰加帕:对大学的资助也是筹码。
克莱因:他们能把持绿卡的人驱逐出境,这是筹码;你因政治腐败而被纽约南区法院调查,也是筹码。
FBI有能力施加影响。根据刚才的描述,FBI可以是个非常可怕的组织。
兰加帕:它成了武器。重要的是,这种以权力为筹码的想法,实际上与单一行政理论非常吻合,后者认为执法部门根本不独立于总统。
克莱因:能说说什么是单一行政理论吗?
兰加帕:这种观点认为,总统,做为单个的人,是所有行政权的体现。他手下所有官员都是这种权力的体现。这等于说,总统可以雇用和解雇行政部门的任何人。
这种观点已延伸到总统可以控制调查,因为他是首席执法官。
宪法第二条没规定必须有独立性,也没提到总检察长和FBI。这些都是从规范中演变而来的。
那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
克莱因:你说到依据单一行政理论,可以对FBI进行利用,请展开谈谈这之间的联系。
兰加帕:单一行政理论支持尼克松的格言:只要是总统做的,就是合法的。
克莱因:讲到这里,我们发现,至少在接下来的中期选举和新国会就职前,川普政府能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
首先,这句话有问题吗?
兰加帕:你比我擅长政治分析,但我觉得有个潜在的制约因素:即使这届政府不在乎法庭,但他们似乎在乎公众舆论。
克莱因:我认为他们不会在乎。
兰加帕:他们不在乎吗?因为我认为大规模抗议、支持率低、糟糕的民调,还有对这些事情的叙述,都有可能(产生影响)。例如,川普不能从萨尔瓦多的古拉格集中营把人弄回来,就暗示他有软弱之处。
因此,我认为有办法让政府在公众叙事中处于守势。
克莱因:让我想想我的看法是怎么转变的,因为我过去也会说和你一样的话。我不会说我认为再大的抗议或再严重的民意流失都无法让他们动摇或感到不安。
公共舆论方面的关键一点在于他无需赢得连任,他的执政方式显示他也不在乎众议院共和党能否连任。
川普有意地牺牲掉支持率,去做一些明显不受欢迎的事情,比如让全球股市崩盘、让美国普通民众面临物价高涨。正是他们相对愿意承受这种不受欢迎和舆论反弹,才让我重新思考他们对这种不受欢迎和反弹有多敏感。
我觉得唯一能阻止他们的是国债市场开始解体。他们不想引发真正的金融危机。
除此之外,他们并不害怕暂时的民调低迷,也对其不敏感。这要么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东西会慢慢变得受欢迎——比如,布克尔在萨尔瓦多是个很受欢迎的总统——要么因为他们认为长远上看,高关税会有效。
我觉得大规模抗议很令人不安。因为我想到川普第一任期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抗议时,川普说他希望国民警卫队或派其他人射杀抗议者,至少朝膝盖开枪。那一命令和建议没被理睬。
川普第一任期时,他身边很多人认为自己工作的一部分是抑制他最糟糕的冲动。但现在他身边没有踩刹车的了,没人会说“不”了。
看看他的内阁如何安排成员给他以北朝鲜“亲爱的领袖”般的赞美;看看道格·伯根姆(Doug Burgum)如何跪拜在川普面前;看看川普提名的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成员如何戴着川普金像章招摇过市;看看国会议员如何提出法案,让川普有可能当三届总统,或在总统山上加川普;看看卢比奥如何为布克尔辩护——这一切除了十分恐怖,也很说明问题。
目前卢比奥显然已完全妥协,或者说,他已选择妥协。川普在国会联席会议讲话中挑出卢比奥,公开嘲讽、公开羞辱。比起其他政府成员,卢比奥明显是如履薄冰。这是个巧妙的策略,向所有人发出信号:卢比奥要么迅速入伙,要么迅速下台。
我认为,他们是在假定这对他们有利的情况下,选择尽可能地利用这一点。只要实际权力没易手,他们几乎没有可被攻击的弱点。
兰加帕:我相信你的评估。
克莱因:我希望自己是错的。
兰加帕:是的,你指出的是,这从来都是忠诚度测试——公开羞辱,让人下跪。
但我认为,正因为如此,抵抗行为才显得更为重要。
哈佛大学拒绝了川普的要求。有律师事务所站出来。还有抗议活动。
如果到了需要发生美国版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地步,也许那就是需要发生的事情。
有时,只有令人震惊的东西才能唤醒人们。
克莱因:是的,这一点我同意。我要说的是,我不认为他们容易受公众舆论的影响。我认为他们容易受权力的影响。
社会上有很多部门掌握着权力。川普并没有绝对的权力。哈佛所做的一切至关重要。其他大学也将开始这样做。因为没人想作为一所没骨气的大学载入史册。
律师事务所开始醒悟了。第一批律所跪了,后面的意识到这是个什么时刻,开始停止下跪,说“不”了。
商界领袖也拥有权力。川普政府明白有很多权力在别人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民主党在中期选举赢得权力非常重要,因为川普政府最终尊重的是权力。
从关税豁免和例外条款可以看出,有些公司是他不想与之为敌的。
我相信抗议是重要的。我相信我们会走到那一步。我只是认为,我们走到那一步时,那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
兰加帕:当然。他会援引《叛乱法》。
克莱因:你想谈谈《叛乱法》允许做什么吗?
兰加帕:《叛乱法》允许总统将军队用于国内执法。因此,我们会看到军队出现在街头,可能逮捕民众或进行其它执法。军方通常不在国内那么做。
克莱因:我也担心他会援引《叛乱法》。他任命黑格塞斯、帕特尔,所传达的信息是,他让忠于他的人负责——
兰加帕:并将军法检察官撤职。
克莱因:将他认为不忠诚的将军撤职——至少企图撤掉一些。
他试图控制安全机构,那不是没有原因的。
兰加帕:对。我只是认为,正如你提到的,从现在到中期选举前,我们定期、有计划地行使这些小块的权力——等到中期选举——[笑]如果我们坚持100天,不知道会是什么局面——[笑]。
克莱因:[叹气]我不想在节目中显得悲观无力,但我要说:如果现在不能阻止川普,以后会更糟。
如果我们不严肃对待眼下的处境——
兰加帕:是的。
克莱因:这都成老生常谈了:“起初,他们来抓共产党员,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然后他们来抓工会会员,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然后他们来抓犹太人,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人为我说话了。”
不是没人了,而是到最后,人们认为发声太危险了。每次对社会上你的敌人中的较弱者行使权力,你的权力都得到加强,最后,没有人能阻止得了你。
这就是为什么阿布雷戈·加西亚一案不是件小事。
兰加帕:不是。
克莱因:那是马里兰一个普通的三孩儿父亲,没人认为他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如果川普能对他那么做,然后在白宫和布克尔坐在一起说:“我也想对美国公民这样做”,而人们只是耸耸肩,然后翻篇儿,那他学到的就是,他可以那么做。
兰加帕:这就是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所说的,权力通常是被赋予那些专制者的,而人们会提前服从。
在我看来,我们肯定已处在“红区”[注],但我们还来得及做很多事情。
[注]red zone,美式橄榄球离端区20码内的区域,是防守的危险区。每当进攻方推进到这个区域时,势必引发恶战——双方寸土不让,激烈交战。
回到智利的例子——因为我是研究拉美的——那个国家经历17年独裁后,摆脱了困境。
所以,总能走出来。只是会越来越难,就像那首诗说的。所以,现在是时候了。
有一种盲目自信,就是以为法院会拯救我们。
克莱因:是的。
兰加帕:法院有它的作用,主要是发挥其机构作用。但法院并不能拯救我们。
其他机构——我指的不仅是政府分支,还有你提到的国会、企业、法律界、大学、新闻界——所有机构和人员在这个时段都必须保持强有力。
克莱因:我常与国会民主党人交谈,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他们实际上没多少好的选择。
我不是处处同情他们做的决定,但除非他们想利用债务上限让经济崩溃,否则没有太多筹码。
他们可以在参议院拖延时间。但事实上,川普政府目前并没有大型立法议程,民主党在参议院不占多数,他们在众议院的权力也很小。人们希望他们拥有他们并不真正拥有的权力。
一年内,政府又将面临关门的问题。按目前的情况发展,民主党很难说出“我们要继续放任自流”这种话。
但这正是其他社会机构的重要之处。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高兴哈佛大学做出这样的反应。那些拥有巨额捐赠却如此轻易就下跪的大学,那些律师事务所,那些在川普第一任期敢于直言、第二任期却决定屈服的商界领袖,我真的对那一切很反感。
马克·扎克伯格几个月前在乔·罗根(Joe Rogan)访谈上说:现在是Facebook回归言论自由的本源的时候了。
眼下的一切难道不正是对言论自由的威胁吗?Facebook的雇员拿着绿卡回美国,因为在他们的手机里发现了批评川普的内容,就被叫进小黑屋,然后被遣返。
川普政策关于言论自由的内容是什么?这些人在这个国家不仅拥有经济资本,还拥有文化资本,何时他们才会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发声?
发声很重要。这些信号发出后,会被其他人注意。每个人都是社会传播的节点。
兰加帕:我不指望扎克伯格在任何事情上坚持原则[笑]。
回到人们希望民主党做他们没有权力做的事情——有些道理。但现在也是一场信息战。
再回到阿布雷戈·加西亚:有些故事可以穿透噪音。共和党就很擅长这个:他们擅长把得到的信息提炼成非常简单的东西,然后重复、重复、再重复。在我看来,川普是个信息战大师。
我们要从中学习。这个案子应该成为那种故事。因为人们正是会因为你提到的原因而明白这一点。人们会明白,如果政府能拦下这个在美国呆了10年的人,把他从车里揪出来,押上飞往萨尔瓦多的飞机,然后不管了——它也能对我们那么做。
克莱因:他们让自己的违法行为通过一个活生生的人展现出来。
兰加帕:他们让他们的违法行为通过一个真实的人展现出来,这是个让人们觉醒的机会。
就连乔恩·斯图尔特都说:你说得对,我以前没把这当回事,现在我要认真起来。
我认为,在这个时刻,会有人认真起来。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