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伦南正义中心的民主计划的负责人Thomas Wolf和计划的律师Ethan Herenstein,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分析了最高法院即将听取的一个案件:摩尔诉哈珀案。
此案基于一个边缘的宪法理论,试图将决定联邦选举的主要权力归于州立法机构,并取消一切的制衡。作者们认为,这个理论几乎没有历史和法律的支持,唯一的支持来自几位大法官的意见,这充分地说明了当今最高法院的极端程度。

最高法院的保守派超级多数成员,上周刚刚在一个鲜为人知但又极其危险的计划上踏出了下一步:试图将对宪法中的选举和选举人条款的极端曲解塞进法律,如果成功,这将在全国范围内造成选举混乱。
在明年夏天之前,以及在2024年总统选举之前,高院可以剥夺州法院和州宪法在为联邦选举制定法律时,制衡州立法者的能力,让党派多数几乎完全控制选民如何投票,以及这些选票如何计算。
而且,这将使目前的高院(在投票权方面已经有一个可怕的记录),成为立法机构行为是否合法的最终裁判。
他们这个项目的核心概念:所谓的独立州立法机构理论(independent-state-legislature theory),处于美国法学的边缘,以至于它的少数支持者,甚至连最起码的判例法和历史碎片都很难找到以加以证实。但高院中的支持者们,似乎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捷径,那就是一个名为摩尔诉哈珀(Moore v. Harper)的案件,他们刚刚将此案列入高院今年秋季开庭的日程。
这个上诉案可追溯到今年2月,当时北卡罗来纳州最高法院撤销了对州内的国会地图的极端党派划分,这将使共和党人在众议院席位的竞争中获得巨大优势。几位共和党州议员要求最高法院为今年春季的初选恢复有偏见的地图。
他们在紧急文件中声称,北卡罗来纳州最高法院甚至无权审查立法机构绘制的国会地图,尽管地图违反了州宪法中的若干保障,因为在他们看来,州法院和州宪法都不应该对联邦选举的运作方式有发言权。
如果立法者的理论听起来很极端,那是因为确实如此,这是基于对宪法条款的严重误读,这些条款规定了管理联邦选举的责任。这些条款将这一权力赋予各州的“立法机构”(同时将制定规则的最终权力保留给国会)。
理论的支持者坚持认为,这些条款赋予了这些立法机构管理联邦选举的专属和几乎无限的权力。普通的民主制衡机制,如行政官员否决法律的权力,以及法院审查和推翻立法机构的行为,就会被抛在一边。
这个理论将在最危险的地方创造一个无法无天的真空,选举。
(注:这条理论取决于对宪法中“立法机构”(legislature)的解读,通常来说,此处指的是基本的立法过程,即在议会通过立法后,仍需要行政机关的州长签署才能成为法律。而且立法一旦违反宪法,州法院可以介入阻止。而不单指议会本身,否则将违反美国三权分立的立国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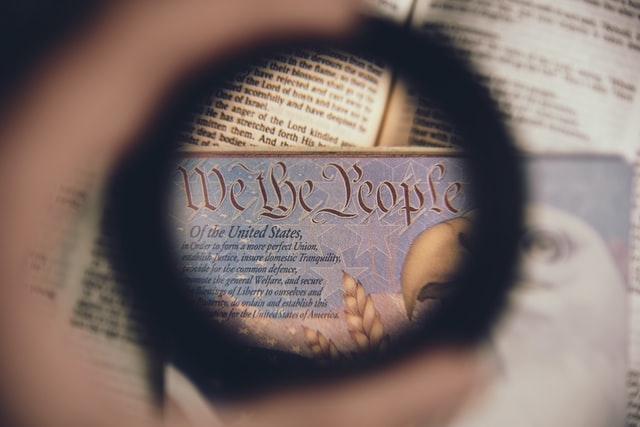
不出所料,潜在的选举颠覆者期望用这个理论,来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这也是特朗普在削弱选举结果有效性的公开运动中的要点。在选举后的采访中,特朗普本人也援引了这一理论,说“各州的立法机构并没有批准对这些选举所做的所有事情”,这也是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哪些选票应该被计算在内的诉讼中,质疑方的一个关键逻辑。
最高法院在2020年秋季驳回了这些法律挑战,这本应是对这项理论的最终说法,但阿利托大、托马斯和戈苏奇大法官一起写了一份“声明”,重新把这个理论带回到桌面,此外还有类似的反对和赞同意见。他们以新的势头将这个理论带回世上,让其迅速回归。
这样一来,这些大法官们凭借自身职位的力量,将这个本该是为绝望的法律挑战而匆忙拼凑的无稽之谈,转化为正当的诉讼立场。他们让北卡罗来纳州的选区划分者,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最高法院惨败后,仍有胆量到美国最高法院试试运气。
3月,法院以未签署的命令拒绝了议员们的紧急请求。但是,托马斯和戈苏奇再次加入阿利托的反对意见,发表了另一份反对意见,要求共和党议员提出全面上诉,以便在2022年选举后将他们的选区划分恢复原状。(布雷特·卡瓦诺法官的同意意见中也是如此)。立法者在10天后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请愿书,引用了阿利托的反对意见,及其本身的微弱引证作为他们的理由。
现在,高院已经回报了他们的努力,将对他们的上诉进行辩论。
正如大多数给予案件听证的决定一样,大法官们没有解释他们受理此案的原因。但阿利托先前的反对意见揭示了推动这一争端的基本动力:几位大法官积极争取机会,尽快将他们的想法变成法律,无论这些想法是多么明显的毫无根据。
阿利托的反对意见,将立法者上诉的核心理论称为“特别重要和反复出现的问题”,即通常应由高院介入并做出决定的问题。但是,如果说这个理论是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那只是因为这些大法官一直在谈论它。
事实上,阿利托大法官为支持这项理论而提供的八条引文中,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反复出现的问题,除了阿利托、托马斯和戈苏奇自己在问问题之外。
阿利托的八条引文中,有四条是关于2020年选举案件的命令,但没有一条支持这项理论。另外四条引文中的三个指向基于这项理论而被驳回的诉讼,第四个则与此无关。没有任何一个案例包含哪怕一丝暗示这项理论可能有价值,或指出有关其正确性的合理语言。
第五次引用的是“布什诉戈尔”(注:高院在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高院引用宪法法第二条的平等保护条款,驳回戈尔要求重新人工计票的要求,使小布什在佛罗里达州的总统选举中获胜)一案的同意意见,甚至不是多数派的意见。
对于这个2000年的案件,当时的高院本身基本都说了,永远不应该被引用来解决任何未来的案件。那份同意意见被高院匆匆掩盖,几十年来一直未被触及,直到卡瓦诺把它扔进2020年选举案的一份同意意见的脚注中。
另外三个是2020年各种选举案件的反对意见和同意意见……分别由阿利托、托马斯和戈苏奇撰写。

更重要的是,阿利托的反对意见,没有引用任何来自联邦审判法庭或上诉法庭的意见来认可这条理论,或证明法庭之间对其正确性的冲突,这是最高法院受理案件的最常见理由。
而且,异议书中也没有引用其他权威,如法律评论文章,而法官可能会参考这些文章来说明一个新颖的、但有效的理论的概要。
这也难怪。在这些大法官开始吹捧这一理论的两年里,大量的学术研究从各种想得到的角度,驳斥了这一理论:宪法文本的明确含义、建国时代无可争议的历史、一个世纪以来从未中断过的实践和先例以及常识。而下级法院之间也不存在有意义的意见分歧,立法者试图绕过这些问题,在他们的文件中加强这个理论,但他们的案件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强大。
换句话说,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基于这个理论的案件能够获胜,除了几位大法官认为它可能会赢的断言。
因此,当阿利托写道,高院“迟早要解决这个问题”时,他并不是在观察法律的现状,也不是因为认为某种难以避免的浪潮迟早将冲击高院,他是在预言自己所创造的危机。
如果高院继续将立法者的理论转化为法律,美国的民主将受到影响。这项理论不仅为极端的选区划分提供了宽泛的许可,使政客们能够违背选民的意愿,永久地巩固自己的地位。还可以创造途径,使各州选举官员制定的基本和必要的法规失效:这些法规确保选举机制的运作,和人们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安全地投票。
这个行动同样可以削弱长期以来的州宪法保护,以确保人们在投票箱前不受歧视,并让他们得以秘密投票。它将把未来制定规则的所有权力放在州立法机构的手中,而州立法机构是当今美国最极端的党派政治行为所在。
它将阻碍州法院解释这些法律的权力,限制州法院根据州宪法审查这些法律是否合法的能力,并将州法院置于期望尽快收复失地的最高法院的监督之下。
称此案的结果会造成混乱,将是一种轻描淡写的说法。
高院仍然可以拒绝这一危险的理论,决定审理一个案件只需要四票,但制定法律需要公开投票中得到五票。到目前为止,大法官们一直在利用其不引人注意的、相对较少的紧急上诉案件备审目录,来推进自己的目的。
不过,在未来,此案将被放在所谓的高院案件日程上,吸引一切有关人士:各方(本案涉及许多人)和法庭之友(注:专业人士对法院不太理解的一些议题提出意见)提出充分的辩论书,公开辩论,以及在媒体和社交媒体上进行数月的审查。
任何最终希望撰写支持独立州立法机构理论的法官,在面对反对独立州立法机构理论的大量事实和法律时,将很难写出可信的意见。任何这样的意见,都将比高院最近被广泛嘲笑的扩大枪支权利和消除宪法对堕胎权保护的意见书,成为更加明显的司法诏令。

现在,需要揭露这些大法官最新计划的无根无据和极端性质,因为公众会意识到这个高院到底有多危险,他们对高院的崇敬会骤然下降。然后,也许那些一直在问他们还愿意走多远的大法官们,会开始问一个不同的问题:他们还能继续支持这种无法持续的做法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