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佐溪
1993年,意大利导演柏纳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拍摄的电影《小活佛》上映,讲述了迦毗罗卫国太子悉达多修行得道成为佛祖释迦牟尼的故事,佛祖的扮演者是后来因《黑客帝国》而走红的基努·里维斯。
在印度裔加拿大导演卡里德·赛义德(Khalid Sayed)看来,相较30年前这种匪夷所思的选角思路(用白人演员扮演有色人种),当下北美影视行业在BIPOC(黑人、原住民、有色人种)议题上已经进步了许多,却仍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
作为一个在两年前流行起来的概念,BIPOC群体正在北美发出越来越高的声量。现在,赛义德和他的团队正在多伦多筹备第二届BIPOC电影节(BIFF),向全世界的创作者征集BIPOC相关的电影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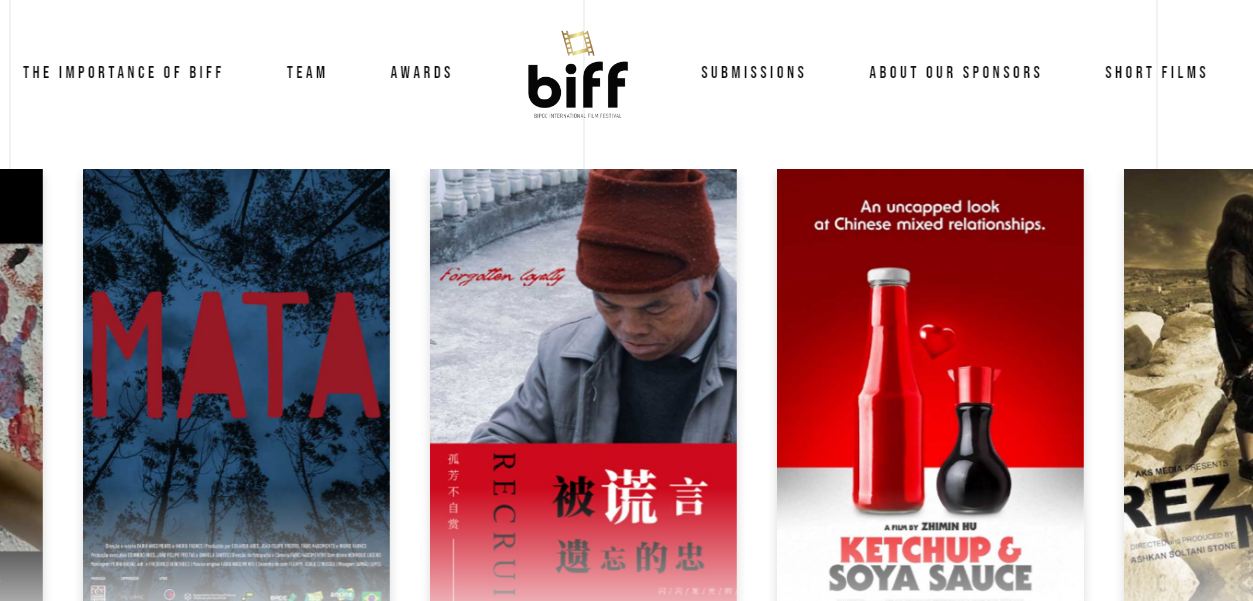
BIFF电影节的评委Melody Shang说道: “我们在努力推广这个概念,是为了在将来不需要去推广这个概念,我们希望在未来,可以不用再提这种身份,每个人对待我们和对待非BIPOC群体是一样的。”
“你不是一个加拿大的加拿大人”
赛义德是加拿大影视制作公司Jamun Media的联合创始人和导演,为丰田、加拿大皇家银行等客户拍摄电视广告,也指导过不少宝莱坞电影和电视剧。他在11年前来到加拿大,成为了一名加拿大公民。
但直到几年前,他还是经常被公开问,有没有加拿大本地的经验。
“现在问这个问题不合法,他们不问了。但这个问题依然存在。”他说,在自己的创作思路得到验证,也得到客户、媒介机构的认可以及官方的批准后,会有人突然对他说:我们想要一个加拿大的导演,你懂的,就是加拿大的加拿大人(Canadian Canadian)。
还有人会问他:“你的英语怎么说得那么好?”他哑然失笑,问对方:“你说的英语好是什么意思?我来自印度最好的大学,我也上英语课,这有什么奇怪的?”
他说:“如果你去香港工作,会有人问你怎么会说粤语吗?如果你去中东地区工作,会有人问你怎么会说阿拉伯语吗?没人会问。人们在那里有平等的机会。”
赛义德觉得,自己以一种仅仅作为BIPOC成员的方式被对待,而这个群体在加拿大的一些大型制作公司、动画片工作室中所占比例很难提升,即使有所提升,也常常只是当作一种象征——他们在那里是被当作是中国专家、印度专家、韩国专家,却从来不是“加拿大的加拿大人”。
“在争取机会的时候,我应该被视为一个加拿大人,而不是一个BIPOC——谁更有才华,谁就应当被雇佣。”他说。
之所以得不到平等的机会,在赛义德看来,是出于一种“移民必须要向我们学习”的思维定势:你不懂这个市场、不懂这块土地、人们的行为方式、饮食习惯、文化,所以你没有机会。“但当你去中东地区、去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非洲工作,你不了解那里的宗教、食物,却能被当作合作伙伴被对待。这种学习应该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

Melody Shang在20年前移民到加拿大,现在是Dreameng Studio的创始人和制作人。在演艺生涯中,她也遇到过不少障碍,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口音。由于她多少带点中国口音,她从未得到过任何重要角色的试镜机会。
“作为第一代移民,我们的障碍就是我们的口音。”Melody说道,“这里有很多电影节,他们说是给亚洲人办的,但很多上交的和选出来的作品,都是美国或者加拿大亚裔加拿大人制作的电影。尽管他们的故事也是关于亚洲的,但他们更倾向于找那些在这里出生的演员去演。”
正因为如此,BIFF电影节对全球的创作者开放,去年的第一届BIFF就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近600部电影作品,为了呈现不同的声音,评委团也包括了非BIPOC成员。
Melody说:“作为第一代移民,我们有自己的口音,也有和我们原本文化更强的连结,我们想要支持的不仅是那些长得和我们像,还有那些跟我们有类似经历的创作者。好莱坞电影所展示的也许是对的,但很多都是过去而非当下的。我们要让更多人知道,如今的中国和印度是什么样子。”

加拿大的国门对全球敞开,但当赛义德深入了解后,却发现并不那么让人满意。他住在密西沙加这个移民城市,当他去到市长办公室,发现政府的团队成员中,没有一个来自于BIPOC群体。
“这里存在一种不能说出口的偏见。”出版人、BIFF电影节的管理总监卡里姆·米兹拉希(Karim Mizrahi)说道,数年前他能听到这些直白的话语,现在的区别是,这些话不再能被说出口。
但斯鲁蒂·加纳帕蒂(Shruti Ganapathy)则觉得,这样的偏见并非没有被说出来,“只是小声说而已,你依然可以听到”。加纳帕蒂是万锦艺术协会的执行总监,也是此次BIFF电影节的执行总监,负责电影节的筹资工作。
常年负责各种艺术活动的推广、和不少艺术家和创作者打交道的加纳帕蒂说:“要把一个黑人或者亚洲艺术家推上舞台,我所不得不要经历的各种繁文缛节非常非常多,但在帮白人艺术家做推广的时候,我却没有遭遇过类似的麻烦。”
有色人种占加拿大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但在加拿大,BIPOC群体在影视制作、生产和发行的方方面面都面临着障碍。

拿原住民群体为例,根据2013年原住民电影制作的报告,2008年到2012年,加拿大电视电影公司(Telefilm Canada)资助的310部电影中,只有5部是由原住民创作的;2008-2012年间,安大略省媒体发展公司(Ontario Medi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支持的115部故事片中,只有一部是由原住民创作的。而根据麦肯锡今年3月的一份报告,在美国从事电影工作的编剧、导演和制片人中,只有约6%是黑人。
赛义德说:“在美国,过去3年中有许多积极的变化,但在加拿大,尽管BIPOC群体在人口上正在逐渐成长为多数人群,这里有仍有巨大的空间需要去填补,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让BIPOC群体更有存在感。”
他认为,在美国、好莱坞、奥斯卡,已经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BIPOC电影工作者,但在加拿大,想要获得更多平等的机会,面临的是迥异的文化。
他拿巴基斯坦裔加拿大导演沙米恩·奥贝德·奇诺伊(Sharmeen Obaid-Chinoy)举例,作为一个两次获得过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导演,即使在加拿大的影视圈,知晓她名字的人也甚少。“我们不会说她是加拿大人,几乎没有人讨论她。”
BIPOC创作者所获预算仅为同行的10%
过去两年中,加拿大政府陆续发布了一些针对BIPOC影视工作者的资助项目。但在加纳帕蒂看来,要获得这笔资金,BIPOC群体要面对的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加纳帕蒂说,作为非BIPOC群体在申请这些项目的时候,往往只需要回答所制作的内容是不是和BIPOC相关这样的问题(大概在3个问题左右),但作为一个BIPOC,却要回答10多个问题。
赛义德也表示,尽管比起前几年,相关的资助更多了,但BIPOC群体要拿到这笔资金,难度比非BIPOC群体大得多。
实际上,这形成了另一种恶性循环。Melody说:“在加拿大,我们能够有一个好演出的机会更少,即使你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制作人,如果没有足够的经费,也很难成功。BIPOC群体中的高净值人群看到这些有限的产出,会觉得我们不够优秀,就不会给我们经济上的帮助。”
在广告制片方面,Melody面对的现实更为直接。一些品牌客户会拍摄不同版本的电视广告(例如中国的、印度的版本),作为华人创立的制作公司,他们所获得的预算仅仅为主流广告工作室的10%。她说:“我们非常勤奋,特别希望证明自己能够做得很好。但我们做着同样的事情,却只拿到十分之一的预算。”
根据麦肯锡的报告,由黑人制片人、编剧和导演主导创作的电影所获得的资金,平均比其他电影少40%。
赛义德认为,BIPOC影视行业从业者和广告公司不应该妥协。“如果这样的话,钱会变得越来越少,因为客户和资助者也知道,这些人不会要求更多,这样一来,大家都只能变得越来越没底线。”
在为BIFF电影节筹资的过程中,加纳帕蒂也倍感艰辛。那些“主流”的电影节主办方很快会拿到一张1万加元-2万加元的支票,但去年的BIFF电影节在找赞助人的时候,沟通起来却非常痛苦。 “你要反复告诉他们,我们和加拿大更相关,更需要被看到。”
“有趣的是,BIPOC是加拿大最大的消费群体之一,我们花了更多的钱去买广告里的产品,拿到的报酬和资助却是相反的。”加纳帕蒂认为,这种现象的存在就是因为BIPOC群体没有真正反对过,而他们正是想通过BIFF传达这样的声音:我们所做出的努力远大于自己应得的部分,我们希望有平等的位置。
努力发声, 是为了将来让BIPOC的概念淡去
6月中旬,网飞宣布推出一项针对加拿大影视创作者的项目,来自弱势群体的七位创作者获得了有偿指导的机会,为网飞的一个原创剧集开发素材,参与者可以获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薪酬。
这也在BIPOC群体中引起了一波讨论,但在不少人看来,这样的举措并不会真正帮助BIPOC群体找到更强烈的存在感。
加纳帕蒂说道:“网飞在美国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们想播出更多BIPOC相关的内容,也有这方面的资助,但要支持这个群体,就得从草根开始,只是帮助金字塔尖的那些人,并不会真正起作用。在加拿大也是同样的情况,加拿大比美国人天性更保守,要接受这个多元化的世界就更有挑战性。我们依然在挣扎。”她说。

BIFF的意义,不仅限于让更多的BIPOC创作者获得更大的平台和机会、提升这一群体的身份认知。在加纳帕蒂看来,全球化的进程在继续,单一叙事无法维系。“如果我们只是从一种角度来讲故事,对于文化融合和文化理解并没有帮助,而这对当今的世界是亟需的。虽然听起来有点滥俗,但这有利于世界的和平。”
她还补充道,近几年,她在加拿大看到不少影视人才的流失,很多人觉得在加拿大找不到合适的机会,最后不得不回到印度。她觉得,现实本不应该这样,这些人应该是出于选择,而不是出于必要性而回到印度。
Melody刚来到加拿大时,听闻加拿大同性婚姻合法化大感震惊,因为在当时的中国,这个是一个敏感群体,甚至不能被公开讨论。但久而久之,她现在觉得这就是一个和空气一样普通的名词。“我希望以后当人们听到BIPOC电影节的时候,他们不会讨论不同肤色的人,而只是把它当成是任何一个人都愿意来参加的电影节。我也希望作为一个制作人,别人在提到我的时候,不是说我来自中国,而是说我很了解中国文化。”
赛义德也希望,几年后,他们可以不再需要用到BIPOC这个词。“黑色、黄色、棕色是颜色,为什么白色就不是颜色了?它们都是色谱上的颜色而已。”
参考资料: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diversity-and-inclusion/black-representation-in-film-and-tv-the-challenges-and-impact-of-increasing-d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