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n Johnson在《外交》发表文章,称中国“一带一路”的政策其实并没有真正帮助到中欧和东欧的国家,导致中国和这个地区的裂痕日益扩大,现在,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更是成了矛盾激化的导火索,欧洲各国领导人都在采取更为疏远和强硬的态度对待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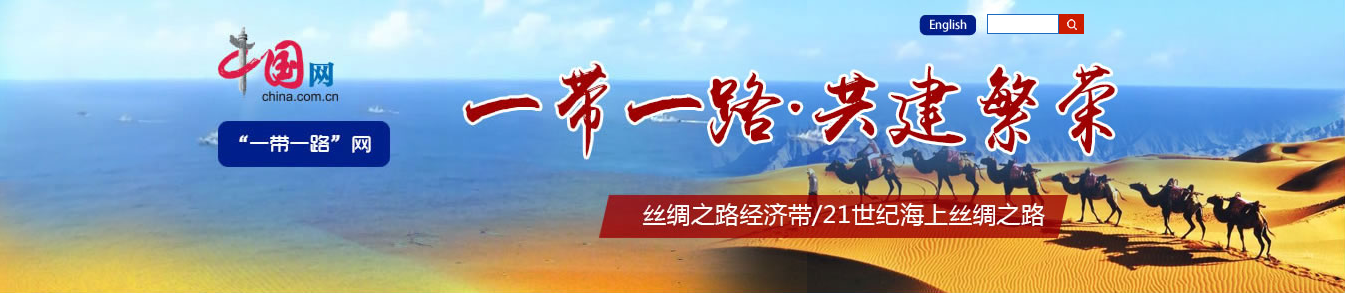
4月和5月,当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进入第三个月时,中国派出一名特使与8名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官员会面。这个时机并非巧合:在俄罗斯发动入侵的两个月里,中国在欧洲的地位降到了新低。
欧洲各国政府对中国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以及对俄罗斯侵略的默许感到失望,中国领导人希望能够在欧洲大陆这个它认为有特殊影响力的地方及时止损。
10年来,中国一直将中东欧国家作为其外交重点。中国官员认为,只要提供最高级别的接触机会,并给予巨大的贸易机会,就可以利用后共产主义政府组成的小团体,来制衡欧盟对中国的批评声音和美国在欧洲大陆的影响。
随着乌克兰战争给中欧关系带来的寒意,中国政府认为在欧洲举行一系列热烈的会议(包括在布达佩斯、布拉格、里加和华沙举行的会议)将有助于扭转局面。然而这些努力毫无结果。相反,中国大使及其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遭到了拒绝,例如,捷克外交部说,利用这次会议表达了“对目前中国与俄罗斯合作的保留意见”。
在乌克兰战争的许多重要连锁反应中,中国和欧洲之间日益严重的裂痕可能是最不被重视的。早些年,中国政府认为,与欧盟不像与美国那样存在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是一个可以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地区。中国政府开始利用它所认为的,与中欧和东欧一大批国家的特殊关系,来巩固这种重商轻政的做法。
对于像中国一样在近几十年来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一些欧洲政府来说,中国是一个强大的新伙伴,并且有可能对其经济进行大规模投资。作为回报,中国政府希望找到进入欧洲巨大市场的后门,并在与美国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新的政治筹码。
然而,今天,欧洲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外交政策难题之一。
在某种程度上,目前的局面是经济的误判造成的,双方都高估了这种安排的潜在利益。并且,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日益僵化的立场使事情变得更糟。中国大陆政府对立陶宛给予台湾少量的象征性承认,进行了报复,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还在同一问题上威胁了其它欧洲政府。
在这些恶化的关系中,中国在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支持,使其在欧洲的麻烦达到了顶点。
这其中的风险并不小。乌克兰战争暴露了中国的盟友有多么少,以及中国领导层在追求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方面发生了多么严重的误判。中国为在欧洲获得影响力而采取的强硬措施也适得其反。尽管中国的经济和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保证了它的实力和关注度,但失败的欧洲项目,证明其无法在先进的民主国家中赢得持久的合作伙伴,这种模式似乎可能会阻碍它在世界的长期影响力。

中国的华沙条约
中国全面的欧洲战略在10年前就已形成,当时中国启动了与中欧和东欧的伙伴关系。这个集团于2012年4月在华沙成立,之后不久被称为“16+1”,因为它由中国和16个欧洲国家组成: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北马其顿、黑山、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
后来一个不属于旧东方集团的国家希腊加入,组织的成员扩大到17个,立陶宛在2021年放弃了这项条约,成员数又回落到了16个。
当时,许多中国分析家认为这一区域性的尝试是一个睿智的举动,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前奏,“一带一路”于次年启动,旨在促进中国在全球的商业和政治联系。在中国前任领导人的领导下,中国一直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和平、注重技术的国家形象,其主要优先事项是融入全球经济而不是投射硬实力。
尽管中国幅员辽阔,政治体制威权,但许多欧洲领导人、以及大众和西门子等欧洲大公司,都认为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国家,正在提供一个巨大的市场。但中国大陆当局的战略目标,如与台湾地区的统一和向南海扩张力量,与欧洲的核心利益相距甚远。
对中国及其欧洲伙伴来说,16+1集团也具有历史意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其欧洲伙伴有着共同的社会主义传统,都处于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的不同阶段。此外,这些小国中有11个是欧盟成员,因此中国可以在不必与西欧的先进经济体直接竞争的前提下,在世界最大的贸易集团中获得一席之地。中国在这些国家建造的工厂有资格进入欧盟内部,从而获得进入欧盟共同市场的特权。与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更发达的国家相比,中国政府更容易在这些国家立足。
中国政府还将“16+1”视为与欧盟本身达成更全面的经济协议的基础。2013年,欧盟和中国开始就所谓的《全面投资协议》进行谈判。经过多年的讨论,在时任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的积极支持下,双方于2020年原则上敲定了这项协议。从表面上看,中国似乎已经走上了与欧洲建立更长期经济关系的道路。
然而,在这一点上,16+1已经被其不明确的目标所束缚。首先,中国和它的欧洲伙伴是带着完全不同的期望加入这项条约的。从一开始,这个项目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主导的。中国建立了一个网站来记录这个项目,并设立了一个完全由中国外交部官员组成的秘书处。
相比之下,这个地区的许多政府,把这种关系仅仅视为是获得中国投资和贸易的一种方式,但并不认同中国政府为自己设定的让自己远离欧盟的目标。中国官方对这项协议的措辞,采用了中国政府话语中模棱两可的陈词滥调,几乎没有阐明这个集团的目标,只是平淡地说,是“基于传统友谊和所有参与者对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的共同愿望”。
相应的,看得见的成果也很少。一个基本问题是,中国认为中东欧国家形成了一个统一的集团,但是16+1所涵盖的区域绵延近2000英里,从北部的爱沙尼亚到南部的希腊,并包括经济条件差异极大的国家。16个国家中有5个国家(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北马其顿、黑山和塞尔维亚)不是欧盟成员,主要是发展水平较低的贫穷国家。
最初使这些国家联合起来的原因,是各国都认同中国提议中的这样一种假设: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将意味着中国资本的大量注入。这些资金将重振没有西方投资者的老工厂和项目。
然而,这些希望几乎没有得到落实的。例如,2013年,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16+1峰会上,中国、匈牙利和塞尔维亚讨论了贝尔格莱德和布达佩斯之间的高速铁路线。这个30亿美元的项目被宣传为欧洲最重要的“一带一路”倡议,被誉为中国新伙伴关系的象征。然而,10年之后,这条铁路线仍未完工,并被卷入腐败和缺乏透明度的指控中。
正如罗马尼亚学者安德烈·布林扎所说,16+1很快就变成了,“一个以大量未兑现的承诺和项目为特色的年度峰会”。

失败的承诺?
根据中国的数字,在2012年至2020年期间,中国与欧洲伙伴之间的贸易每年增长8%,在疫情期间增长更快。但这一增长是在一个非常低的基础上开始的,其结果也是极其不显眼的。根据捷克研究员理查德·图尔恰的说法,中国目前占中东欧地区出口的不到2%,进口的9%。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影响更小,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不到1%。
图尔恰指出,这意味着中欧和东欧“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相比,以其经济互动的份额来衡量,中国的存在是最少的”。鉴于中国为培养这一地区所做的长达十年的努力,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糟糕结果。
结果如此惨淡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做法其实是把实际的投资工作留给了中国企业。虽然许多中国公司是国有企业,但仍然是以盈利为导向的。而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中欧和东欧根本没有什么吸引力。与西欧相比,它的人口密度较低,城市分散在大片地区,基础设施较少,生活水平也较低。难怪尽管中国政府在口头上表示鼓励,但很少有中国公司接受在这些地区进行投资的呼吁。
从广义上看,中国在欧洲的失误反映了一种政策制定方法,这种方法在中国背景下是行得通的,但在海外并不一定奏效,特别是在政府对选民直接负责的民主国家。中国的许多倡议往往是炫耀性的,开始时轰轰烈烈,并报告创造性的统计数据。他们提供的是意向性声明,而不是具体的计划。具体内容是后来添加的,有时是在几年后,或者根本就没有。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对外交政策和贸易的重商主义做法,即将外交关系建立在对经济利益的计算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所有国家都会这样做,但在大国中,像中国这样如此严重地依赖经济关系来塑造对外关系的做法,是比较少见的。
与此同时,中国宣布的项目往往变成了“大材小用”或死胡同。除了高铁项目,这些项目还包括罗马尼亚切尔纳沃达核电站156亿美元的扩建项目,中国承诺的投资从未兑现。2020年,在中国签署这项协议七年后,这个项目被一个美国财团接管。罗马尼亚政府去年禁止中国公司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投标,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核电站的失败。这个地区的其他政府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认为中国的竞标合同,不利于它们与更先进的工业经济体竞争。
在台湾问题上的较量
但中国在欧洲的支持率下降并不仅仅是因为经济上的失败。许多欧洲政府对中国利用经济实力来压制对其政策和人权记录的批评感到越来越无奈。这种胁迫策略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以立陶宛为例。为了尊重中国大陆政府,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大多数国家都使用“台北”一词,来描述台湾在他们国家的任何代表处,他们的想法是,使用台湾地区的首都而不是其名称是可以接受的,因为直接用名称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国家地位。
当立陶宛去年决定无视这一惯例,允许台湾使用“台湾”一词开设代表处时,中国政府以对立陶宛的全面经济禁令作为回应,不仅切断了立陶宛对中国的出口,还威胁要禁止在其他国家生产的任何产品,只要产品中含有立陶宛的成分。
立陶宛拒绝向中国的要求低头,起初,在欧洲几乎找不到什么支持立陶宛的国家,在中国威胁要制裁使用立陶宛制造的部件的国际公司之后,情况更是如此。一些欧盟国家(包括与中国有大量贸易往来的德国)向立陶宛施加非正式压力,要求立陶宛在亲台立场上做出退让。
然而,渐渐地,欧洲领导人发现中国的强硬行为是不可容忍的。2022年1月,欧盟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诉讼,指责中国从事歧视性行为,因为其停止为立陶宛货物通关,并拒绝立陶宛的进口申请。正是在这些不断恶化的关系中,乌克兰战争使许多欧洲政府更加果断地反对中国。

俄罗斯比欧洲更重要?
中国政府在入侵前对俄罗斯的支持让许多欧洲领导人感到惊讶。
就在战争开始前,中国和俄罗斯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赞同俄罗斯要求北约退回到1997年边界的呼吁。如果这种提议成真,使捷克共和国、波兰、斯洛伐克和波罗的海国家等国家(它们都是中国16+1集团的成员)将失去北约的武器和军队,变得像乌克兰一样脆弱。
自战争爆发以来,中国的行为——即重复俄罗斯的观点,入侵是由北约扩大所挑起的,使欧洲各国日益增长的不安变得更加清晰。3月,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博克说,这场战争表明,“片面的经济结盟实际上使我们很脆弱,不仅仅是在俄罗斯方面。”
欧洲对中国的失望,在4月初中国高级领导人和欧洲议会的一次峰会后暴发了。欧盟负责外交事务的最高代表约瑟夫·博雷尔,称这是一次“与聋子的对话”。这些情绪在“16+1”成员国中尤为强烈,其中许多国家现在正处于与俄罗斯对峙的前线,本身也受益于北约的安全保障。
一些欧洲国家现在已经公开拥护立陶宛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一个是捷克共和国,也是这个地区最富有的国家之一。4月,捷克外交部长扬·利帕夫斯基要求对中国大陆当局支持俄罗斯的行为进行更严格的审查,指责中国“欺负”台湾,并呼吁加强捷克与台湾的关系。立陶宛的近邻拉脱维亚则呼吁中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值得注意的是,“16+1”本身似乎正在失去活力。去年,6个成员国决定不让他们的国家元首参加与中国领导人的虚拟峰会,而是派出较低级别的官员。今年,16+1峰会没有举行,可能是因为乌克兰的战争。
中国在中欧和东欧的失败,凸显了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在外交事务上越来越多的意识形态化做法。这些失败大多是自己造成的。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怀疑西方联盟,如北约,但其公开支持俄罗斯立场的决定更进一步,本质上是在告诉16+1的国家放弃其关键的外交政策之一。
中国外交政策机构的人一定认识到这在当地会造成多么糟糕的作用,但他们显然无法动摇领导人。相反,习近平希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协议,他与普京有着密切的个人关系,因此俄罗斯胜出。这种行为使中国外交政策专家遭到了排挤,而更接近中国领导人的意识形态的人士得到了支持。
在经济领域,在欧洲不太富裕的国家投资,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挑战。但中国不愿意将有问题的项目完成,导致问题变得更糟。然而,“16+1峰会”仍在继续,这个组织的中文网站上列出了同样支离破碎的目标。
中国对欧洲的强硬态度可能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中欧和东欧与中国打过交道的分析家和官员说,中国官员正在努力加强与这个有着各种语言和文化的地区的联系。尽管中国特使上个月对这个地区的访问被认为是失败的,但中国领导层会继续坚持、不会放弃。
然而,成功将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回归到更加务实的政策。由于习可能会在今年秋天关键的党代会上获得又一个五年任期,这种路线修正可能还得等一段时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