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邀请了一系列学者来思考“美国权力的未来”,普林斯顿大学的政策和国际关系学院的前院长,智库“新美国”的执行总裁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的文章认为,美国的未来的力量来自于它多元化的人民,以及他们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如果美国能够善用多元化的力量而不是让它分裂国家,美国将仍然能够维持世界领袖的地位。

里根时期的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曾经告诉我,要始终关注人口学,以了解世界和塑造未来的力量。来自阿富汗的严峻影像,突出了美国军事力量的局限性,以及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工具间的不匹配
。然而,美国力量的未来远非取决于军事力量,而是取决于美国国内发生的人口变化。在未来20年里,美国将从一个白人占多数的国家演变成一个“多民族国家”:一个没有一个种族或民族群体占多数的国家。
美国或者是弄清楚应该如何利用这一点、并借此连接世界的巨大好处,或者允许种群间的紧张关系将其撕裂。
看看任何一张流入和流出美国的地图,无论是金钱、货物、服务、人员和数据的流动,最粗的线总是流向欧洲。再看看军事联盟、领事馆或姐妹城市的地图,美国与欧洲的联系密度将再次凸显。这并不是一个偶然。因为在1870年至1900年期间,近1100万欧洲移民来到美国,还有大约25万来自亚洲,主要来自中国,还有近10万来自中美洲和南美洲。
在此期间,美国人口基本上翻了一番,从3800万增至7600万。到1900年,美国人口中还包括约900万非裔美国人,他们几乎都是被奴役者的后裔,被迫与他们的家庭和部落分开,并被强行带到美国,使大多数人无法追溯他们的起源,更不用说与他们的祖国建立经济或文化联系。
所以,在20世纪中,新一轮的移民克服了大量的偏见和障碍,定居并融入了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当他们向国外寻求资本、市场、思想、旅行和历史时,几乎必然会转向“老家”,这几乎总是意味着欧洲。
但现在不是了。
在1965年至1990年期间,另一个巨大的移民潮进入美国,但这一次他们绝大多数来自中美洲和南美洲、亚洲和非洲。移一旦来到这里,移民就会做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找工作,上学,成家,竞选公职,积累财富和权力。
一路上,他们会与任何来自“老家”的亲戚、朋友和联系人联系,使商业、文化和公民网络的链条更加紧密。2017年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美国一个州的新近移民只要增加10%,就会使从其原籍国的进口增加1.2%,对其出口增加0.8%。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2015年的一项研究进一步表明:“从某个国家进入当地劳动力市场的移民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使这个地区的企业向那个国家出口的服务增加6%至10%。”
今天,18岁以下的美国人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自认为是白人。到2027年,即美国成立250周年后的一年,30岁以下的人都将如此。在2040年代的某个时候,美国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一个没有多数种族或族裔的国家。作为一个国家,美国人与各大洲的家庭和文化联系的分布将更加平等,这些联系是经济增长和外交及文化影响力的潜在途径。
然而,为了充分利用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好处,美国人将不得不对身份和权力进行不同的思考。
20世纪见证了从大熔炉到多元文化的转变,从“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到“更多种多样”(plures)的转变。在21世纪,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成功的关键是,将美国人的身份定义为多元身份,与其他群体或国家形成同心或交叉的认同圈。
美国人可以同时是 “多”和“一”,这种宽广的身份概念,将使我们能够与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根联系起来,庆祝我们多元的文化,同时为一个足以容纳我们所有人的国家感到自豪。

为了使这样的想法成为现实,我们必须设想并实施一个真正的21世纪的移民政策,不仅仅是为移入的居民,也为移出的和在多个国家保持居住权的人。目标是吸引人才,但也要与母国分享这些人才,允许美国公民和居民在各个国家来回工作和生活。
这一愿景似乎是美国保守派最糟糕的噩梦,是特朗普和他的后继者非常残酷和成功地操纵的所有恐惧的具体化。事实上,英国前首相特雷莎·梅也对这种多重身份的想法嗤之以鼻,她声称,“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你就不是任何地方的公民。”
她触及了一个真正的担忧。全球化爱好者如果是以牺牲本土为代价来拥抱全球,将会犯下巨大的错误。正如英国政治评论家大卫·古德哈特(David Goodhart)所说,“来自于某个地方”,即庆祝和支持扎根于一个或多个现实社区的本地身份,同时也从在全世界各地的在线和线下生活和工作中受益,这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正如大流行病所表明的,我们可以在一个地方生活和投资,同时在另一个地方工作。
权力也可以更加多元化。
美国的外交政策官员和战略家,应该从等级森严的权力观念转变为更加横向的权力观念,从山顶之王转变为网络中心。美国作为“全球警察”的形象总是被夸大,但20世纪的美国外交政策精英和国际关系学者肯定将美国视为全球霸主:要么是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要么是独立的霸主。作为一个霸主,需要运用强制的硬实力和吸引式的软实力,将它们融合在各种巧妙的权力概念中。
然而,权力也可以用联系来衡量,承担起作为一个充满建设性的、富有成效的,即深且广的关系网的职责。美国应该创建一个新的全球服务机构,来代替现在的外交服务机构,这是一个创建于1922年,至今基本没有变化的机构。
如果建立一个看起来更像全世界的外交使团,讲世界各地的语言,从出生就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或者至少通过家庭关系了解其他文化的代表团,将在与全球人民建立牢固的关系方面将有巨大的优势。正如在20世纪让欧裔美国人学习接收他们的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很重要一样,我们应该期待在21世纪看到非裔美国人讲普通话,西裔美国人讲阿拉伯语,或者阿拉伯裔美国人讲俄语。
在军事领域,一个更加多样化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领导人团队,应该像这一代人对欧洲战争的前景感到恐惧和关切一样,去思考中东、非洲、亚洲或拉丁美洲的战争。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军队可能死亡或受伤,而是因为更广泛地认识到任何地区的冲突,对平民,对那些在历史上或在目前与美国家庭有联系的平民意味着什么。
这些新的精英们也将带来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
像我一样在20世纪下半叶长大的欧洲裔美国人,很难将美国使用武力与帝国主义的过度扩张或与代表腐败的干预联系起来。而西裔美国人、阿拉伯裔美国人或非裔美国人却能够做到,因为他们的家庭往往来自那些美国军事冒险造成更多负面经历的国家。
与参加过长达数十年、充其量是毫无结果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老兵一起,他们的关注点可能更多的是在建立美国的威慑能力,旨在成为全球知名的避免或防止战争的国家,而不是赢得战争。
而这种威慑能力又将再次依赖于联系的力量。前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米歇尔·弗卢努瓦认为,国防部应投资于“一个安全和有弹性的‘网络状的网络’,用于所谓的C4ISR:指挥(command)、控制(control)、通信(communications)、计算机(computers)、情报(intelligence)、监视(surveillance)和侦察(reconnaissance)。”
“网络状的网络”,定义和描述了我们大家越来越多地生活和工作的虚拟世界。网络力量是战略连接和断开连接的力量。它是多元的、多中心的,其范围和力量来自于它的用途。为了在自己的人民中取得成功,并获得世界人民的尊重,美国必须从警察转变为问题解决者,成为政府和非政府层面的核心力量,完成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等事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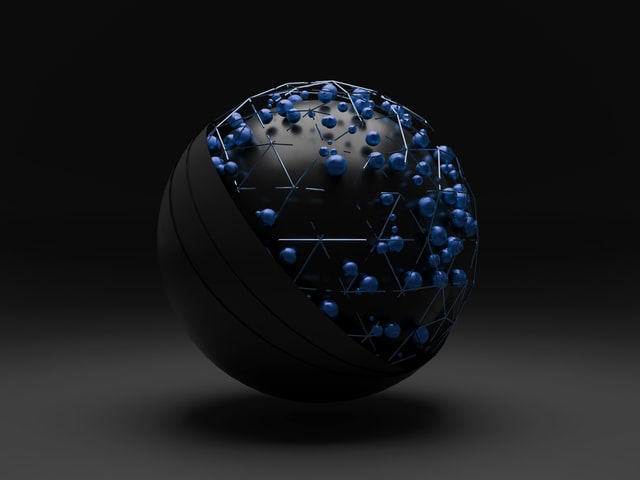
实现七国集团关于全球最低公司税的协议是正确的例子。与欧盟和其他国家合作,通过确保公司支付其公平份额,取得有利于各地公民的结果。成功的解决全球问题,意味着从中心而不是从顶端开始领导,关注人民间的成果而不是国家之间的权力游戏。
一个多元化的美国,不仅会增强其经济、外交和军事力量,随着其发展反映世界所有文化的艺术、文学、电影、音乐和其他类型的媒体,美国的文化力量也会大大增强。比如,如果美国能够充分挖掘女性的才能,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巨大利益,那些如果仍在母国就无法发挥潜力的女性,在美国可以与家乡的朋友建立商业、文化和政治的联系。
有趣的是,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了解网络的力量,基于亲属关系、商业和文化的联系。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计划明确提到需要“充分发挥港澳台和海外华侨华人……的独特作用”。一带一路本身就是一个基于在世界各地建设基础设施和其他联系的宏伟战略。有意思的是,两年前,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的数量超过了美国。
然而,由于其自身的人口力量,中国也可能正在建立一系列非常不同的联系,其人口正在快速老化。根据一些研究,由于中国家庭对男性的偏好,中国“消失”的女性人数与加拿大的全部人口一样多,约为3500万,原因是被迫堕胎(或更糟)。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男人已经在亚洲各地寻找新娘,其中许多人是被贩卖的。
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并不是注定能成功。为美国带来如此大的希望的人口和技术力量,也可能使这个国家分裂,政治上的两极分化已经使国会几乎瘫痪。植根于不信任和恐惧的分歧,部分反映了美国白人多数群体的许多成员,认为他们会失去什么,以及各种少数群体的许多成员认为他们会得到什么。
共和党内公开的白人至上主义政治的崛起并不是偶然。它对美国政治的整体影响将远远超过欧洲中相似的极端政党,因为美国的两党制和“胜者通吃”的政治制度功能失调,往往选出的人得不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民主理念的核心是相信每个美国人都有平等的投票机会,而且选举必须是自由和公平的。同样重要的是,选举制度应保证获胜的候选人实际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而不仅仅是不到半数的多数得票。如果不进行改革,如采用排序选择投票和多成员国会选区制度,以及结束选区划分,美国很可能会来回摇摆,陷入日益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功能障碍。
如果美国能够战胜自身的小恶魔,它就能驾驭一种新的全球力量。
拜登在就任总统三个月后向国会发表的第一次讲话中,谈到了“赢得21世纪”的必要性。他听众中的婴儿潮一代(二战后至60年代中旬出生的人)可能赞同他的观点,即美国是一个胜利的民主国家,正在庆祝战胜专制的中国和俄罗斯。
但是,对于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千禧一代(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来说,他们的生活已经被一场全球大流行病深深打乱,他们担心在本世纪内是否还能居住在一个可居住的星球上,这种语言就像谈论“欧洲协调”(19世纪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各国协商出的外交机制)一样陈旧。在他们看来,“胜利”不是一个国家击败另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人们在面对生存威胁下能否生存甚至是获得繁荣。
塔利班推翻了美国为建立和维持了20年的阿富汗民选政府,这将使试图通过军事力量来领导世界的期望愈加破灭。许多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实际上都同意“美国第一”的说法,即使他们对美国是什么和应该成为什么,有着非常不同的定义和愿景。
“克制”的口号正在兴起,换言之是 “负责任的治国之道”。

然而,克制并不是一种战略。它可能会建议不要做什么,但它并没有为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提供一个积极的处方,对其他国家来说也是一样。因此,对美国力量进行新的定义和展望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21世纪,美国处于独特的地位,可以利用其与世界各国人民的联系,释放他们的力量、才能和创新,以应对已存在的全球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