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记者贾斯汀·凌(Justin Ling)在《外交政策》上发表长文,反驳了当下广为流传的关于新冠起源的“实验室泄露”理论,他认为这个理论是由政客和阴谋论者鼓吹和媒体炒作的结果,并不具有太多实际证据。加美编译,不代表本站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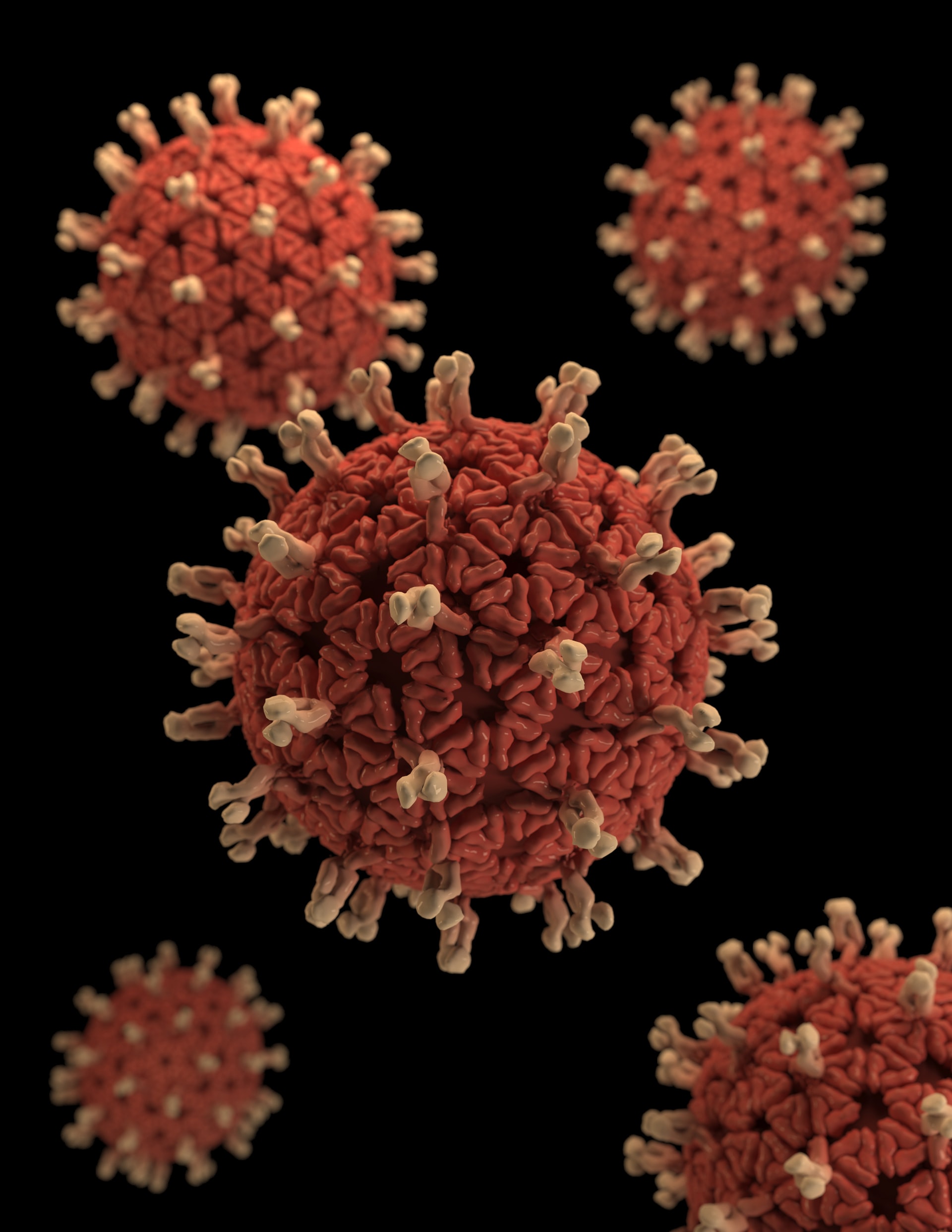
每一种大流行病的背后都有一个关于其阴暗起源的故事。
当艾滋病毒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时,有一种由苏联推动的说法,称这种病毒是在美国的一个实验室开发的。由于华盛顿对这一疾病的不作为,和其不光彩的实验历史,此理论的支持者们说,这一理论不能被轻易否定。
在许多早期蜱虫传播的莱姆病病例,首次在长岛湾附近被发现后,人们认为美国军方的梅花岛动物研究实验室同样位于长岛湾的一个岛屿上,这也太巧合了。
当非典肺炎在2003年出现时,人们对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的非自然来源的担忧,也随之而来。
“这是一次非常不寻常的爆发,”生物武器专家肯·阿利貝克(Ken Alibek)当时告诉《纽约时报》:“很难说它是故意的还是自然的。”
一位俄罗斯科学家认为,“非典型肺炎的传播,很可能是由亚洲细菌武器实验室培育的战斗病毒的泄漏造成的。”
近年来,消除埃博拉病毒的努力,因针对医护人员的攻击而受阻,其动机至少有一部分是有人认为该病毒是人为的。
将疾病归咎于人类,是一项古老的传统。因病毒从起点到第一次被检测到的地方,会沿着一条复杂的路径,难以被追踪。在没有确定的答案的情况下,人类喜欢编造故事,从14世纪的黑死病到2009年的H1N1疫情。
在缺乏确定性的情况下,对于病毒学来说,这两套理论,自然的或人为的看来都是合理的,就像薛定谔的猫。
然而,当传染病能够被解释时,自然几乎总是罪魁祸首。在非典出现后,科学家们怀疑冠状病毒从一只蝙蝠跳到了另一种哺乳动物,可能是果子狸,但无法解释它是如何出现在中国广东省佛山的一个农场的。
疫情爆发十多年后,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住在云南省蝙蝠遍布的洞穴附近的村民,距离疫情初次爆发的地方大约900英里,尽管他们从未被感染过,但带却有大量的非典抗体。虽然几乎不可能弄清楚非典是如何传播到那么远的,但科学家们现在相当肯定,病毒的旅程是从那个山洞开始的,然后再传给了一种哺乳动物,最终感染了一个人。
蝙蝠很可能在埃博拉病毒的潜伏方面也起到了关键作用。1999年,在黑猩猩身上发现了一种与人类非常相似的艾滋病毒菌株,尽管目前仍不清楚它究竟是何时转移到人类身上的。埃博拉病毒或莱姆病的真正源头也仍然不确定,我们也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但我们知道的是,它们几乎肯定不是来自美国政府的实验室。
但当然,有时政府确实会在不知情的平民身上做实验。有时病毒也确实会从实验室里泄露出来。
然而尽管实验室外泄的情况确实发生过,绝大多数都被迅速控制。因恶意或无能而导致的严重爆发的例子少之又少。唯一已知的例子之一可以追溯到1977年,当时一个以前被消灭的H1N1病毒株再次出现,估计是由于苏联的疫苗计划出了问题。
鉴于这段历史,出现围绕新冠的所谓实验室起源的理论并不奇怪。但是这一次,它不仅仅是豪无根据的猜测。它被美国政府的一些最高层,以及热衷于新说法的媒体视为一种严肃的可能性。

实验室泄露理论的证据和传播
当2019年12月首次检测到新管病毒时,中国政府以其一贯的方式作出回应:压制和保密。而后数周的掩盖突然转为全国范围的遏制。这种仓促的保密手法引起了联想:他们还在隐藏什么?
没过多久,网络侦探们就提出了一项令人信服的证据:武汉病毒研究所,也就是那个帮助找出非典可能起源的单位,其距离第一次报公开的疫情病例只有大约9英里。
2020年1月,该理论开始于边缘状态,其指控存在一个秘密的生物武器项目。在几周内,这个理论在一个可疑并声名狼藉的网络上一发不可收拾,除了问题和推测外一无所有。他们说,主流媒体的沉默是其同谋的证据。
他们抓住了在疫情蔓延时的早期混乱中出现的零星证据,如一篇后来被撤回的论文,该论文表明HIV基因被插入了病毒中。
然后,这个理论找到了一个强大的组织。福克斯新闻在2020年4月报道说,美国情报界对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的想法“越来越有信心”,也许不是作为生物武器,而是意外泄漏的结果。时任总统的特朗普在回应福克斯时,忸怩地赞同了这一理论。
到了那年5月,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承诺提供“结论性”证据来支持这一假说。
这个结论性的证据并没有出现。
相反,有一些可疑的档案和更多的消息来源,在谈论美国17个情报机构中的“大多数”对实验室泄密理论的“认同”。《纽约时报》后来报道说,当时的国家安全副顾问博明(Matthew Pottinger)很早就赞同实验室泄密的理论,并一直在向情报机构施加压力以支持他的观点。
但在报道这一理论的同时,许多媒体也将其视为阴谋论而予以否定。一次常规实验室事故的可能性,被卷入了关于生物武器和细菌战的理论中。科学家们热衷于把辩论的焦点放在如何应对大流行病上,而不是地缘政治的争斗。
出现了一些间接证据来支持这一理论,例如国务院电报报告了2018年武汉实验室的安全问题,尽管电报全文并不如报道头条那么危言耸听。然而,理论支持者们的重大主张并没有得到证实。没有一个来自五眼联盟的成员国,认为此理论正变得更加可信,澳大利亚甚至直接反驳,美国情报界的其他部分也是如此。
但随着特朗普政府的垮台,政权前成员认为推动这一理论是为未来积累可信度的途径。
2020年12月底,博明告诉英国保守党议员,“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该实验室可能是最可信的病毒来源”,这个理论再次出现在英国媒体上。一位保守党议员报告说,博明曾说过,一位中国的吹哨人正在向美国政府提供该理论的证据。
蓬佩奥的国务院在那个时候的推出一份“概况介绍”,虽然比蓬佩奥本人的说法更含糊,承认病毒的来源是自然的还是人祸尚不确定,也同时也更绝对,报告说“(武汉病毒研究所)内部的几位研究人员在2019年秋天,在第一个确定的疫情案例之前就已经生病,症状与新冠和普通季节性疾病都一致。”
然后猜测就来了。
今年1月,小说家尼科尔森·贝克(Nicholson Baker)在《纽约杂志》上提出了他的结论。“非典2型不是作为一种生物武器设计的。但我认为,它还是被设计出来的。”
贝克提供了一个惊人般详细的,但仅仅是猜测性的理论。它是这样的:2012年,云南省墨江市一个铜矿的工人从蝙蝠粪便中感染了一种当时未知的疾病。该病毒的样本—特别是他们命名为RaTG13的一种新型病毒—被运回武汉,并在那里进行了实验,包括改变其尖峰蛋白。然后,贝克写道,该病毒可能已经“出去了”。
5月,《原子科学家公报》加入了这场争论,前《纽约时报》记者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的一篇文章与贝克的假设不谋而合,以前他曾提出过一些与种族有关的可疑基因理论。
他正确地指出,许多冠状病毒,如那些导致新冠和非典的病毒,起源于云南省的山洞中。但他争辩说,如果这是自然现象,为什么会在近1000英里外才爆发?
他同时认为:“蝙蝠的活动范围是50公里,所以不太可能有蝙蝠到达武汉。”
关于该病毒本身的生物学特性,他写道,弗林蛋白酶裂解位点,该病毒上的一组极小的氨基酸与人类的弗林酶相连接,使其能够直接感染我们,是证明该病毒的起源为实验室的一个线索。贝克指出,有两种方法可以使这种裂解位点自然地附着在病毒上:通过病毒本身的突变,或通过一种叫做重组的过程与另一种冠状病毒融合。
韦德甚至在引用了一位坚持认为“重组在这些病毒中自然非常、非常频繁”的病毒学家的话后,依旧得出结论说这两种解释都是不可能的。相反,韦德写道:“那就只剩下功能增益实验了。”
“功能增益”是一个在最近几周得到大量宣传的短语。一般来说,这个过程包括强迫一种病毒在实验室中进化和变异,模仿并强化它在现实世界中可能面临的条件,主要是为了了解这种变异是如何在自然界发生的。
这种做法是有风险的,但不是被禁止的,美国也在进行这类实验。
贝克、韦德和其他人提出的理论是非常复杂的,他们确实抓住了事实的要素,正如他们告诉外国记者的:中国的传染病研究是保密的,而且风险比它该有的要大。武汉实验室确实发现了一种冠状病毒,它被称为RaTG13。墨江的工人确实在2012年患上了一种神秘的肺炎,促使武汉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更加深入地研究隐藏在这些洞穴中的病毒。

然而,除了这些零碎的真相,一切都只是猜测。
这个理论的闸门打开了。《华尔街日报》再利用了关于武汉实验室工作人员生病的报道。《纽约杂志》谴责“自由派媒体”对这个理论推动者的排斥和污蔑。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是病毒来自实验室并可能有军事渊源这一理论的早期支持者,他欢庆自己被平反。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将功能增益理论拖入关于疫情的听证会,声称美国帮助资助这些实验。
学者马修·伊格莱西亚斯(Matthew Yglesias)写道,这种怀疑和驳斥,成就了“媒体的实验室泄露闹剧。”
5月26日,拜登命令他的顾问们“加倍”努力,寻找有关病毒来源的信息。七国集团峰会提出了一份联合声明呼吁进行进一步调查,而拜登说,该病毒可能是“一个出错的实验”。
局外人看来,可能性的天平似乎倾斜了。曾经在2020年初,大量的证据都指向新冠的自然起源,但现在实验室泄露理论却占了上风。
但这是一个幻觉。尽管有相反的声明,但很少有新的、确凿的证据指向实验室泄漏理论。我们有的还是从中国的失职中得出的相同结论,相同的间接证据,以及一个推测性的理论。
这些都不意味着实验室泄密是不可能的,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根本不存在。
在犹他大学研究进化病毒学的斯蒂芬·戈德斯坦(Stephen Goldstein)说:“我不认为我们在过去几个月里学到了什么新东西。我们完全缺乏证据。”
迄今为止,很少,也许只有几篇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认真对待过实验室泄漏的想法。与此同时,已经有许多可靠的研究指出新冠病毒的自然来源。2020年3月发表在《自然医学》上的一项详尽的研究发现,新冠病毒不是在实验室被构建,“也不是刻意被操纵的病毒。”
该论文的作者之一克里斯蒂安·G·安德森(Kristian G. Andersen)在一份声明中说,论文中的结论“此后才被更多的证据进一步加强,而这些证据是非常多的。”
实验室泄密理论最有效的部分之一,不是证据的质量,而是数量。在能够充分讨论或分析之前,一些碎片就被快速地丢出来,其中一些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以生病的实验室工作人员的报告为例,戈德斯坦提出:“在流感季节,一个庞大的研究人员群体中,有三个人出现了类似流感的症状,这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考虑到背景,那强调工人“曾经就医”的简短标题就不成立了。在中国,基础保健主要通过医院提供,而且病假条是强制性的。在武汉去医院看病相当于在美国去看医生。
反对派的依据
谢丽尔·罗夫(Cheryl Rofer)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当了35年的化学家,专门从事军备控制工作。她多年来在严格控制和高度保密的实验室环境中处理钚。她说:“如果这些人在从事武器项目,或功能增益研究,或任何类似的工作时生病,他们才不会去医院。”
即使是实验室与疫情爆发地点相近这一可疑巧合也很薄弱。现在还不能确定武汉是病毒的起源地,而不仅仅是它首次被检测到的地方。与非典一样,即使它跳到了人类身上,病毒也可能起源于数百英里之外,在中国不发达的农村医疗系统中没被注意到。2003年的非典的传播路径,就否决了韦德关于所涉距离太远无法传播的说法。
最近,《每日邮报》和《纽约邮报》大肆宣传一项“爆炸性”的新研究,据称该研究提供了新冠病毒是人造的确切证据。该论文的一位作者告诉《每日邮报》,病毒基因构成中的四个带正电的氨基酸是关键证据,该作者对邮报表示::“物理定律意味着四个带正电的氨基酸不可能处在同一排。 得到这个结果的唯一方法是人为地制造它。”
科学家们不遗余力地粉碎了这个说法。一位称其为“难以置信的废话”,并指出人体中三分之一的蛋白质都具有这种特性。另一位指出,“即使是人造的东西也必须遵守物理学定律”。
“事情已经彻底变得疯狂了,”罗夫说。“即使聪明人也会迷失方向。”

关于情报界已经得出结论的说法也必须以谨慎和疑问的眼光来看待。
美国的情报部门包含大量的机构,有些机构的命中率比其他机构高得多,但没有一个机构的职能是为了解决复杂的科学问题。一篇详尽的《名利场》专题报道,深究了情报界的调查,或者说缺乏调查的情况,此文为贝克和韦德提供的同样微不足道的证据带来了大量的宣传。
这篇文章为蓬佩奥关于实验室泄密的“巨大”证据的轻率说法,提供了背景故事。该报道披露,国务院军控、核查和合规局内部的一个团队最近在今年1月就一直在努力追寻这一理论的依据。专题报道称,当时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福特,“对他们的调查太过敌视,以至于他们认为他是一个一心想要为中国的渎职行为洗白的盲目官员”。
在长篇反驳中,福特指出,他实际上支持实验室泄漏理论,他的主要罪行似乎是坚持将新冠病毒是实验室泄漏的结论交给独立专家。他在当时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当这些独立专家看了国务院的分析报告后,发现报告仅仅建立在由“一位病理学家,而不是病毒学家、流行病学家或传染病模型专家”准备的单一统计分析上。在不具备建立这类模型的专家的情况下,福特认为:“统计学上的案例似乎很薄弱。
CNN报道了类似的问题。“他们的工作方式太过可疑,”一位消息人士告诉CNN,并补充说,“感觉就像他们只是为了证明预先确定的结论而捕风捉影,并把可以批评其‘科学’的专家排除在外。”
罗夫非常清楚地知道,糟糕的实验室安保会导致事故发生。她讲述了1968年美国军队在犹他州进行的秘密化学武器试验导致6000只羊死亡的故事。甚至“洛斯阿拉莫斯也发生了几起钚事故,”当然,世界上也出现过因实验室泄漏而导致的炭疽和非典病例。
不同的是,这些都是已知的病毒和化合物。1977年爆发的H1N1似乎是由于疫苗试验的结果,在试图给士兵接种时,苏联人大概意外地感染了他们。
在最正面的情况下,实验室泄密理论认为中国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危险的冠状病毒,且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对其进行测序或开发疫苗,然后在没有注意到或未能控制它的情况下让它流出。
对这项工作保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武汉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经常与美国和加拿大的同行合作进行冠状病毒研究,我们之所以知道安全方面的缺陷,是因为美国官员参观了这些设施。武汉病毒研究所经常公布其冠状病毒研究的结果,是中国成为科学超级大国目标的一部分。我们之所以对冠状病毒有如此多的了解,是因为武汉实验室对云南山洞的研究。
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真正线索,不是地缘政治而是科学。
实验室泄漏理论说,弗林裂解位点,即病毒上的一串微小的氨基酸,是了解这种新型冠状病毒起源的关键。
戈德斯坦同意。但是,他说,那个裂解位点实际上指向了病毒的自然起源。
他告诉我:“在正常的细胞培养中,并不可能保持弗林酶的裂解部位。”
当新冠病毒在实验室的细胞培养中被复制时,弗林裂解点往往会自我删除。4月底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同行评议的论文指出了这一情况,并确定了其他七篇发现类似删除的论文。
因此,如果研究人员使用传统方法和他们偏好的细胞系,试图迫使病毒复制、变异和改变,那么弗林裂解位点很可能会消失。
功能增益的支持者说,这个弗林位点对人类来说适应性太强,不可能是一个意外。但戈尔茨坦说事实恰恰相反。该裂解位点是不完美的,如此古怪,它只可能是自然界的一个怪胎。
他说:“没有一个病毒学家会使用这个裂解点。”
戈德斯坦补充说,虽然有可能在实验室中复制病毒,同时保留裂解位点,但这会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行事。”而且,最关键的是,这将需要科学家们选择复制病毒速度更慢的细胞培养物。
因此,研究人员将不得不做出一系列低效和奇怪的决定,以保存一种微小的、新颖的、奇怪的酶。事实上,4月《自然》杂志文章背后的伦敦帝国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该病毒的穗状蛋白中增加了四个氨基酸,“发生在它从动物库中出现的过程中,并创造了一个次优的弗林蛋白酶(裂解位点)”。
1月份发表在《干细胞研究》上的另一项研究证明了这些弗林位点是如何在许多冠状病毒中自然演变的。
那么RaTG13呢,韦德和贝克认为该病毒与新冠病毒非常相似,只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即可?
在2020年4月的一份声明中,爱德华·霍姆斯·悉尼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和病毒学家指出,“SARS-CoV-2和RaTG13之间的基因组序列分歧程度相当于平均50年(至少20年)的进化变化。”
霍姆斯说: “因此,SARS-CoV-2不是来自RaTG13,野生动物中冠状病毒的丰富性、多样性和进化强烈地表明,这种病毒是自然起源的。”
戈德斯坦说:“把50年的进化过程塞进8年是不可能的。强迫1000个核苷酸变化……就是,不行。”
但是,也许这项功能增益研究并没有试图在培养皿中复制病毒,而是用活体动物来繁殖和变异病毒—用一只生病的动物来感染下一只,再下一只,再下一只,直到培养出一种进化完整的高效病毒。
沿着这条理论走下去,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玄乎。戈德斯坦问:“还想要搞得多复杂?”
这将大大增加成本,需要密集的劳动力,而且难以隐藏。实验室将需要运行一个名副其实的动物园来完善这种人畜共患的传播。而且它仍然无法解释必要的数十年进化时间。
在2019年12月疫情爆发之前,任何实验室都没有报告过与新冠病毒相似的病毒。自从它出现以来,经过数以亿计的感染,也只网罗了少数几个严重的突变和变种。
“在病毒学方面,我们还不足以制造出完美的病毒,”戈德斯坦说。
然而,大自然却有这个能力。
我们现有的最佳理论是,新冠病毒可能起源于蝙蝠,很可能来自产生非典的同一个洞穴,并在传至人类之前接触过其他两种动物。这三个宿主导致了一种“复杂的进化重组模式”。研究人员在穿山甲和浣熊犬中发现了新冠病毒的近亲,使它们成为所谓溢出事件的主要嫌犯。
虽然武汉海鲜市场在这一流行病中的作用仍不清楚,它是否真的是起源,或者只是第一次大爆发,但新的研究表明它可能是证明自然起源理论的关键。尽管北京方面坚持声称市场上没有饲养活体动物,但《科学报告》的一篇新论文揭示了湿货市场上饲养浣熊犬的照片证据。研究人员发现,“几乎所有的动物都是活体出售,被关在笼子里,堆放在一起,而且条件很差。”
这一理论将意味着新冠病毒曾在三种不同的动物之间跳跃,并传播大约1,000英里。
与非典相比。该病毒在人类间爆发之前,经历了两只动物,传播了大约900英里。

要使实验室泄密理论成立,武汉实验室需要在野外发现一种完全新颖的、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并在不告诉任何人的情况下将其保存在实验室中,或者设计一种高级病毒,将几十年的进化过程压缩进短短的几年内,此举也会震惊技术更先进的美国实验室的科学家。
然后,还需要有一个灾难性的安保协议破坏行为,使实验室的一名或多名工作人员受到感染—但同时,这个事故并不引人注意,所以他们只是在下班后走出了大楼。
戈尔茨坦说:“这虽然听起来比另一种说法单纯,但当你深入了解时,它要复杂得多。
我们又该相信谁?
彼得·本·恩巴雷克(Peter Ben Embarek)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名食品安全专家,他被这个国际主义组织选中,飞往武汉,调查病毒的起源。
“我们的想法是进行必要的研究,以便更好地了解病毒的来源,”本·恩巴雷克在一月份告诉我。他和他的团队正准备前往中国,并不知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场疫情。
他说:“我们的方法正是不遵循任何假说。”
科学证实了新冠病毒是一种“自然病毒”,而不是生物武器。但他承认,“意外发生了”,那么他们就不能不考虑它是从实验室中逃出来的想法。
我问他关于实验室泄漏的理论。本·恩巴雷克说:“他们说的‘越来越多的证据’,我们还没有看到它。
在2月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经过几周的实地考察,本·恩巴雷克和他的同事们宣布,他们已经看到了足够的证据,可以得出结论,实验室泄漏理论是“极其不可能的”。
本·恩巴雷克当时指出:“关于这种病毒没有任何出版论文,没有报告,也没有关于另一种与此极为相关的病毒在世界任何其他实验室中被研究。”
世卫组织研究的科学结论似乎令人信服。但当然,该组织的结论,对许多人来说只是证明了事实的反面,因为世卫组织得到了北京的大量支持。但世卫组织的工作人员自己说,中国政府阻挠了调查。政府试图管理研究人员和记者所能看到的东西。在堪培拉呼吁对冠状病毒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之后,中国政府对澳大利亚进行了惩罚。
但是,中国的保密性和倾向掩盖的做法,并不能证明有什么特别的阴谋,这种偏执是北京的默认做法。
中国官员在发生灾难后总是争先恐后地逃避责任,无论是因自然还是其他方面。
例如,在2008年的四川地震后,一些孩子在地震中死亡家长因抗议被逮捕,试图调查豆腐渣工程的记者被拘留和审查。这种情况也发生在2015年的天津爆炸和2011年的温州火车失事事件中。而且,这种情况每天都发生在较小的、不为人注意的悲剧中。个别官员急于避免成为替罪羊,而中央政府则试图展示一个简单的、精心宣传的有能力且富有同情心的形象。
中国试图掩盖非典,淡化病例数,甚至禁止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人员访问最初的爆发地点。正如一位中国政治专家在2003年告诉《纽约时报》的那样,非典“成为政府的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医疗问题。”
历史在2020年重演,当局压制了那些试图对可能的“第二次非典”爆发发出警报的人,例如已故医生李文亮。
当涉及到中国共产党时,掩盖真相是正常的事情。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与许多研究人员、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谈过。他们对新冠病毒起源的看法一般分为两个阵营。大多数人说,这种病毒很可能是自然形成的,围绕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理论是一种可能的解释,但可能性不高。另一派是少数人,他们说两种理论或多或少都有道理,而实验室泄漏理论急需更多调查。
这两个阵营都很难被指责。
但并非所有的研究都是平等的。
例如,贝克和韦德都引用了生物科学资源项目背后的夫妻二人,该项目在去年夏天发表了一篇宣传墨江矿工理论的论文。然而,该项目主要关注作物科学,并推崇垃圾科学和关于转基因生物的错误信息。自疫情开始以来,这个组织已转向对付他们所谓的“病毒工业综合体。”
一篇经常被引用的社论,是由一些并不擅长病毒学的研究人员撰写的。《名利场》的报道中引用的专家团队大多是匿名的。另一个著名的网页为这一论点汇编了证据,贝克和韦德严重依赖这一网页,但该网页完全是匿名制作的。
当然,许多共和党人对实验室泄密理论的明显偏爱,也很难与他们认为中国是全球安全威胁的默认立场中剥离出来。
一些人,包括我自己,是否在早期就对实验室泄密理论过于轻率地不屑一顾?一个理论的正确性是否会因推崇它的人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的坏人,或古怪理论家们而被影响?当然,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可能性没有被积极探索,事实是,并没有一个压制对武汉实验室的调查或猜测的大阴谋。
然而,即使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实验室泄密理论正确的几率,仍然与一年前报道时大致相同,理论上是可能的,但远不如人畜共患病的可能性。
这种病毒的来源的确很重要。如果北京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负有责任,它就应该接受后果,即便不是,中国仍然需要对其混淆视听的行为负责。
如果云南的洞穴和周围的生态系统在20年内给我们带来了两种高传染性的冠状病毒,那么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下一个这样的冠状病毒,或者从哪里出现。
如果新冠病毒像以前的病毒一样,在各种动物之间传播,沿途间完善了其感染人类的能力,那么它就表明了人类对自然界的入侵,正在以令人担忧的速度发掘出新的病原体。这要求我们对如何在地球上生活以及如何管理野生自然进行实质性的反思。
当然,这是比简单地指责北京更令人不安的前景。
绝对肯定地发现新冠病毒的准确来源或许是不可能的。但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让科学而不是炒作或焦虑来决定可能的情况。
正如罗夫告诉我的那样。“我们都感到失去了控制。而了解这一点的方法就是理解起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