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April Wang
上周五一大早,加拿大原住民艺术家塔玛拉·贝尔就和12岁的儿子匆匆离开了家。在看到坎卢普斯寄宿学校发现215名原住民儿童遗体的新闻后,贝尔说,她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感到很震惊。
为了纪念这些孩子,贝尔和儿子一家店一家店地浏览,购买这些孩子可能会穿的鞋子。他们买的不同款式的运动鞋、靴子和软皮鞋装满了六个大袋子。贝尔说,这些鞋子种类繁多,代表了这些原住民的传统和现代习俗。
“我只是一直在想,我必须做一些事情……作为一个民族,我们需要愈合。我们需要有一个地方来治愈,我们不能只是独自承受痛苦”,贝尔说。

到了中午,贝尔和其他原住民制作了纪念碑,并把215双鞋放在温哥华艺术馆前面的台阶上。后来,纪念馆前又有人留下几十个花束、蜡烛、毯子和娃娃。
和贝尔在温哥华留下纪念物一样,加拿大各地的人们纷纷摆放童鞋、娃娃等寄托哀思:在阿博茨福德的画廊外,在萨斯卡通的市政厅台阶上,在渥太华,在莫霍克天主教堂的门前。
冰山一角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前主席穆雷·辛克莱尔(Murray Sinclair)说,可能会在其他寄宿学校所在地发现更多儿童遗体,人们应该为此做好准备。
辛克莱尔希望幸存者和所有其他人都应当明白,这些信息对于所有加拿大人了解这一经历的真相有多么的重要。
他说:“自从坎卢普斯发生的事情被揭露后,我就被幸存者的电话淹没了。数以百计的电话,往往只是为了哭泣。”
“我不仅能听到他们的痛苦,还能听到他们的愤怒,因为没有人相信他们所说的故事。我能感觉到,他们已经有点失去希望了。他们曾经认为,也许那些没有回来的孩子还可能被找到。可是,他们现在知道这可能不会发生了。”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超过15万名原住民儿童被安置在这种寄宿学校。至少有4100名儿童在上学期间死亡,即每50名学生中就有至少1名死亡。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估计,实际死亡人数可能为6000人或更高。其中至少有821人是在阿尔伯塔省死亡。
皇家山大学负责土著化和非殖民化的副校长琳达·曼斯(Linda Many Guns)是寄宿学校幸存者的后代。她说,研究表明,许多父母从未被告知他们的孩子发生了什么事,需要进行广泛的调查,才能揭开许多学生的故事。
冰山之下:加拿大不愿讲述的历史
如今,加拿大民众对原住民和来自其他大陆的定居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刻。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原住民组织不断增加,宪法对原住民及其权利予以确认,加拿大政府和原住民团体达成新的条约以尊重原住民对其家园内经济发展的监督,最高法院做出一系列保护原住民的重要法律裁决。
然而,对于大众来说,对加拿大过去所作所为的简化和理想化比比皆是。很多人认为,加拿大宪法里那句让人充满力量的“和平、秩序和善治”(“Peace, Order, and Good Government”),正体现了加拿大对原住民政策的实践。
事实上,暴力、混乱和管理不善以及殖民政府般的做法,才是加拿大政府与原住民打交道的特点。

尽管,1867年加拿大“诞生”后遵循了此前英国制定的政策和做法,与原住民签订条约,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原住民的主权及其对领土的所有权。但问题在于,原住民认为这些条约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平协议,而加拿大政府却认为是房地产交易,目的是为了消除原住民对土地所有权的要求,并获得其土地上的资源。
在实践中,加拿大用各种方法来切割这些土地,或将其出租给伐木或采矿公司。原住民几乎从来没有得到这些土地的全部市场价值。
1876年的《印第安人法案》(The Indian Act),将所有当时与原住民有关的立法合并到一起,单方面使国家成为原住民的监护人。而这个法案以及随后的修正案,原住民自己也无法参与。
《印第安人法案》禁止原住民在公共场合穿戴传统服饰,禁止渔堰等传统经济活动。该法案还定义了“印第安人”,创建了一个叫做“有身份的印第安人”的法律类别。在美国,身份标准是由原住民民族决定的。而在加拿大,原住民身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加拿大国家决定的。
拥有身份影响到一个人是否可以生活在原住民保留地,是否能够获得条约权利,享受政府项目,而那些没有身份的人就被剥夺了获得这些福利的机会。
针对这种身份制,原住民作家托马斯·金问道,“你们到底不喜欢我们什么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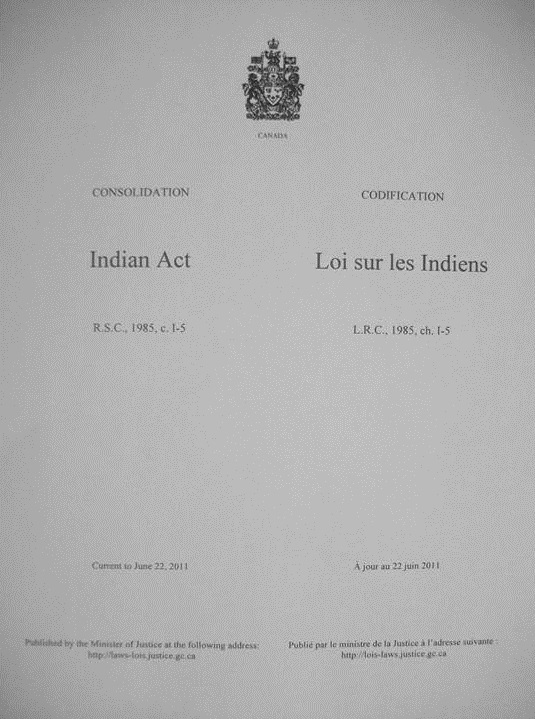
时任加拿大印第安事务副主管的邓肯·坎贝尔·斯科特(Duncan Campbell Scott)在任期内对原住民采取了强制性的政策和具有破坏性的立法限制,特别是在文化和教育压制方面。
历史学家苏珊·奈兰说道,“斯科特想杀死原住民心中的‘印第安人’, 想让原住民摆脱土著的身份认同以解决‘印第安人问题’。这看似没有从身体上杀人,但这难道不是种族灭绝吗?当我们用同化、文化渗透等词来形容它时,难道我们不是在进行文化灭绝吗?”
原住民寄宿学校噩梦
对许多原住民来说,将原住民儿童从家里带走并强迫他们进入印第安寄宿学校的历史,意味着人生、民族和文化的毁灭。
1886年,《印第安人法案》的一项修正案规定原住民儿童必须上学。于是,基督教会和加拿大政府合作创建了“印第安人寄宿学校”(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s),将儿童与他们的父母、社区、语言和传统隔离开来,目的是同化、基督教化这些原住民儿童,并使他们融入加拿大社会。
但事实上,这些学校在教育方面非常失败,学术课程仅限于初、中级水平,大多数学生至少有一半时间在工作——砍柴、耕作、缝纫或洗衣服。过度拥挤、环境不卫生、虐待、性侵是很多原住民儿童的噩梦。
很多经历过寄宿学校的原住民幸存者患上了“寄宿学校综合症”:反复出现恶梦,睡眠困难,注意力受损,回避任何可能使其想起寄宿学校经历的东西,与他人严重疏远,对原住民文化活动的兴趣和参与减弱,对传统文化和技能的了解明显不足。与此同时,他们也无法融入白人社会,在夹缝中成为缺乏身份认同的人群。
然而,寄宿学校对几代原住民造成的创伤从90年代才开始被外界所知。

联邦政府道歉却不愿承担法律责任
1990年,原住民第一民族领袖菲尔·方丹(Phil Fontaine),首次公开谈论他在寄宿学校时被性侵和虐待的经历。随后,教会正式道歉,超过10000名幸存者提起诉讼,时任总理哈珀最终在2008年做出正式道歉。
2008年,加拿大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听取了6500多名证人的证词,创建了寄宿学校系统的历史记录,举办了7次全国性活动,让加拿大公众参与进来了解寄宿学校的历史,纪念那些儿童及其家人的经历。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于2015年关闭时,提出94项“行动呼吁”(Calls to Action),要求各级政府从儿童福利、文化教育、健康、司法公正等方面共同修复住宿学校造成的伤害,并开始和解进程。
然而,这一进程还任重道远。
一方面,加拿大原住民事务部长贝内特周三宣布,联邦政府准备拨款2700万加元,用于帮助原住民社区寻找和纪念在寄宿学校遇难的儿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6月1日也发表讲话,称加拿大人不能闭上眼睛假装这一切没有发生,他们必须承认,国家没有尽到对这些儿童、他们的家庭和社区的责任。
而另一方面,不列颠哥伦比亚省105个原住民提起诉讼,要求联邦政府对寄宿学校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联邦政府在法庭中却否认了任何法律责任,并称这些语言和文化是被“历史、个人和社会环境”以及“土著社区和主流文化”之间的互动所侵蚀,同时也被城市化所侵蚀。
当然,直面历史的黑暗面可能要付出代价,不管是情感上的、经济上的还是道德上的。但回避历史黑暗面的代价将是,压迫和不平等的继续以及正义永远的缺席。
参考资料:
https://www.thecanadianencyclopedia.ca/en/article/peace-order-and-good-government
https://bcmj.org/articles/residential-school-syndrome
https://www.cbc.ca/news/canada/calgary/residential-school-graves-alberta-1.60463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