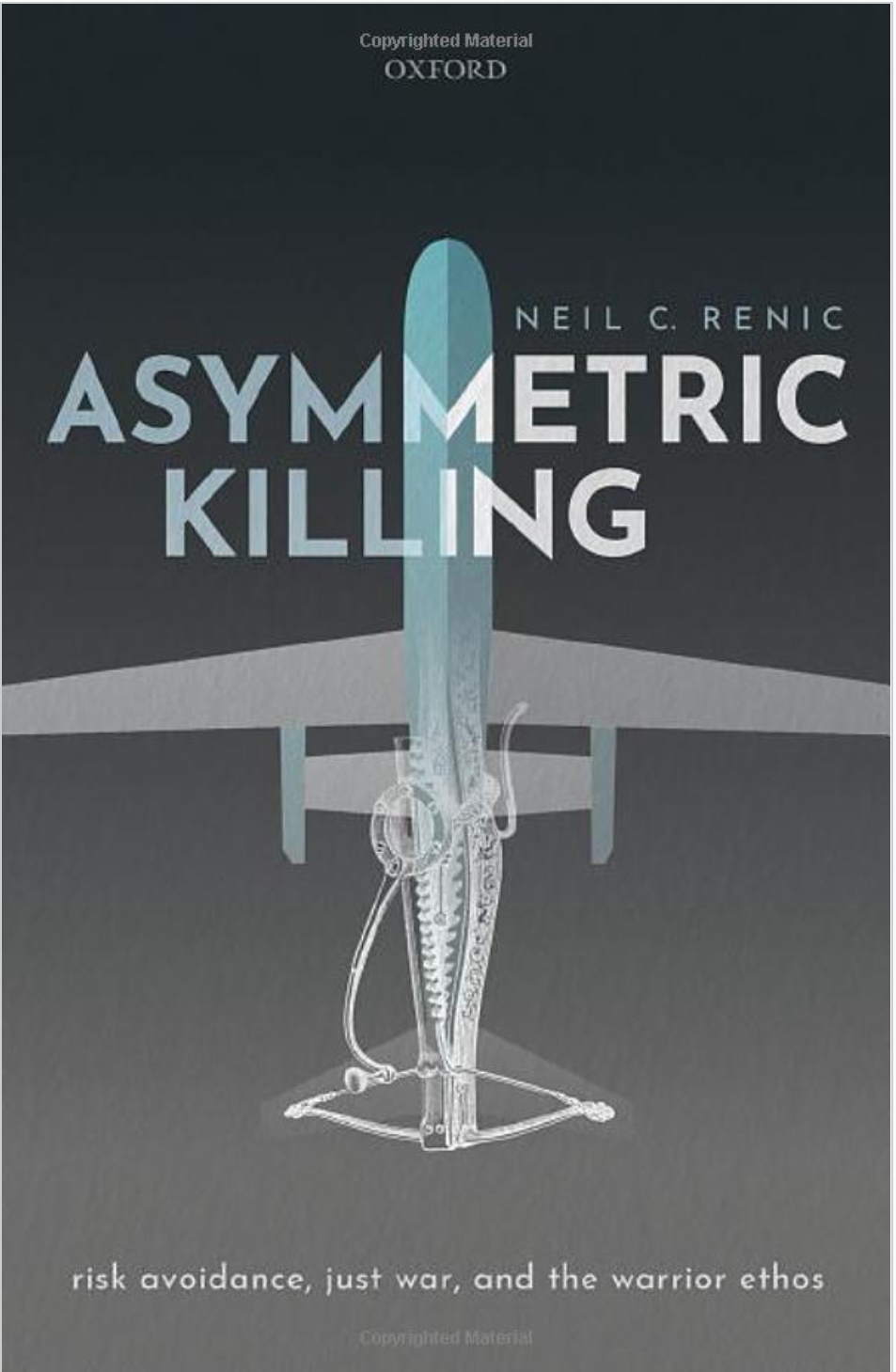
文章载于《纽约客》
作者:By Anand Gopal
编译:远奇
2017年的四个月里,以美国为首的叙利亚联军向伊斯兰国人口稠密的首都拉卡投下了约1万枚炸弹。这座拥有30万人口的城市近80%被毁。
我在ISIS放弃控制权后不久就去了那里,发现那里的破坏规模之大令人震惊:倒塌的公寓楼只剩下钢筋轮廓,被烧焦的学校,还有裂开的弹坑。晾衣绳在散落的立柱之间织成了蜘蛛网,这表明幸存者还生活在这片废墟中。没有人知道有多少居民死亡,或者有多少人现在无家可归或被困在轮椅上。可以肯定的是,对拉卡的摧残与二战以来美国冲突中的任何一次都不同。
这场战争的目标是一个一心想推翻整个人类秩序的敌人,战争显然针对的是反对理性的虚无主义暴动,但拉卡毕竟不是诺曼底。叙利亚人不惜牺牲生命与ISIS勇敢地作战,但美国,除了地面上的几百名特种部队,主要依靠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空中力量,保持安全距离进行战争,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美国人死亡。
美国偶尔会进行常规的地面作战,比如2004年在伊拉克费卢杰,美军曾与叛乱分子在那里展开激烈交火。但拉卡之战是一场在数千英里外的控制室里进行的战争,或是数千英尺高空的飞机上进行的战争,才是现代美国作战的真实写照。
我们已经习惯于通过战争过程中的行为来判断战争的性质。联合国坚持禁止酷刑、强奸和劫持人质等行为的战争准则。当交战双方尽可能避免伤害平民时,人权组织和国际律师倾向于将这场战争定义为“人道的”。
然而,在国际关系学者尼尔·瑞尼克撰写的《非对称杀戮:风险规避、正义战争和勇士精神》(牛津大学出版)一书中,对这一标准提出了挑战。他认为,在评估一场战争的人性时,我们不仅应该关注平民的命运,还应该关注战斗人员是否在战场上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瑞尼克认为,当一方完全脱离危险时,即使它竭尽全力保护平民,这场战争也违背了人道战争的精神。
瑞尼克总结说,“美国式杀戮,日益贫乏、官僚化和超脱”,更像是审判和惩罚,而不是任何传统意义上的战争。
人道战争的核心原则是,战斗人员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互相杀害,值得注意的是,失去战斗力,或者战斗力已经不值一提的人是不能伤害的,并且必须避免以平民为目标。人们很容易认为,平民之所以享受这种受保护的地位,是因为他们是无辜的,但正如瑞尼克指出的,平民“养活了饥饿的军队,选举了好战的领导人,教育了未来的战士。”
在民众革命的发源地叙利亚,整个城镇都被动员起来为参加战争。平民,甚至是儿童,都扮演着放哨、武器走私和间谍的角色。所以,判断一个人在战争中是否无辜,关键是看他在战争中的危险系数。当一个人拿起武器的那一刻,无论是否穿着制服,他都构成了直接和立即的危险。这才是武装人员与平民之间的本质区别。
但如果交战双方本身并不构成直接和立即的危险呢?瑞尼克认为,在巴基斯坦这样的战区,美国人部署无人机杀敌,很少涉足战场,地面上的叛乱分子根本无法反击,这意味着,就构成的威胁而言,这些叛乱分子与平民没有什么不同。瑞尼克认为,向一群开着车的叛乱分子发射地狱导弹与消灭一个开着皮卡去野餐的家庭一样,都是错误的。
有人可能会说,巴基斯坦塔利班虽然对美国士兵构不成什么威胁,但是直接威胁了巴基斯坦的平民。但瑞尼克认为,美国避开战场的做法,实际上已经把平民变成了叛乱分子的目标。无论这种说法正确与否,毫无风险的战斗显然已经把战争带入了新的道德领域,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我们旧有的战场是非观。如果我们仅凭战斗人员对其他战斗人员构成的危险作为区分战士和平民的标准,那么现代战争的远距离暴力就是不人道的。
瑞尼克总结说,“美国式杀戮,日益贫乏、官僚化和超脱”,更像是审判和惩罚,而不是任何传统意义上的战争。
在奥巴马最近的回忆录中,他写道,作为总统,他希望拯救穆斯林世界“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他们“因绝望、无知、荣耀宗教的梦想以及周围环境的暴力所扭曲和限制”。然而他却声称,由于他们生活的地方,以及他所掌握的战争机器,他最终 “反而杀死了他们”。抛开奥巴马这种有点粗暴的概括,雷尼克认为,奥巴马确实可以通过“严格限制 ”远程战争来拯救他们。
学者和人权活动家正在抗议美国最近的海外冲突所造成的破坏,瑞尼克的书只是这群呼声中的一部分。他们的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问题:我们如何利用规则使战争更人性化?
瑞尼克关注的是道德规则,而其他学者和人权活动家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法律法规上。在拉卡战役之后,国际特赦组织和其他组织在废墟中仔细检查,判断这些轰炸是否符合战争法。这项工作是有益的,但其背后隐藏着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在我们努力使战场符合规则的过程中,我们是否忽视了有关战争本质的更深层次的道德真理?
战争应受规则统治的观念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奥古斯丁(古罗马帝国时期天主教思想家)时期,他认为只有一个合法的统治者,在良好意图和正义理由的前提下,才可以发动战争。在中世纪,教会试图禁止弩箭,并努力保护教会财产和非战斗人员免受战争暴力的侵害。但直到19世纪,各国才试图制定法律和条约来规范战时行为。
在美国内战期间,联邦实施了《利伯法典》(Lieber Code),该法典试图限制对敌人施加的不必要折磨,例如酷刑或毒杀。该法典还将“军事必要性”原则奉为法律惯例:为了赢得战争而使用的暴力,才是被允许的。在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公约》中,世界大国在坚持军事必要性原则的同时,对战时行为进行了大致的限制。各国同意暂停使用没什么杀伤力的气球炸弹(利用热气球,绑上炸弹,靠风力进入目标区域实施伤害),但对战术价值卓越的机动飞机的问题保持沉默。
许多国家依然无视这些已经非常宽松的规定。《海牙公约》禁止使用“窒息性气体”,但世界大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中公然藐视这些公约。这些公约还明确宣布故意攻击平民为非法行为,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交战各方已经认识到轰炸城镇和村庄的军事优势。
1942年,英国的战略不是瞄准军事设施,转而命令士兵袭击德国城市的工人阶级地区,正如丘吉尔后来所说:“为了增加恐怖。”
1943年,美英两国空军向汉堡进行了长达7个晚上的狂轰滥炸,造成58000平民的死亡。城市轰炸让数百万无家可归、饱受炮弹袭击的德国人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游荡。泽巴尔德(W. G. Sebald,当今最有影响的德国作家之一)后来将这片土地描述为“一个神秘的史前的坟场,它脱离了文明和历史,回到了游牧采集者的进化阶段。”
接着是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造成大约25万人死亡。盟军的恐怖袭击总共夺走了大约50万平民的生命。这种模式在朝鲜战争中仍在继续,美国国务卿迪安·拉斯克后来回忆说,美国轰炸了“每一块砖,每一片瓦,每一个活物。”
在越南战争期间,第一次出现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强大的反战运动。通过电视,美莱大屠杀之类的新闻直接送到了美国人的客厅里,受到良心谴责的拒绝服兵役者和反战活动人士求助于国际法,以证明他们反对大屠杀的合理性。
他们在塑造美国战争行为方面的成绩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大。战后,五角大楼用激光制导弹药等发明改造了军火库,这种武器可以进行“精确打击”。美国军方开始遵循《海牙公约》以及其他条约的原则,这些联合规定被称为《武装冲突法》。美国的恐怖轰炸已成为过去。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数百名专业律师与将军们一起坐在位于沙特阿拉伯等地的中央司令部总部,以确保美国遵守战争的法律规则。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时律师部署。
在摩苏尔战役中,敌方狙击手爬上摩苏尔大学前工程学院院长穆罕默德·莱拉家的屋顶。据邻居说,他和妻子冲上楼,恳求他们离开。一瞬间,一枚弹头夷平了房屋,杀死了楼下的狙击手,莱拉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女儿全都被炸死了。
从表面上看,对法律的严格遵守是人道战争事业的胜利。然而,叙利亚的废墟讲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故事。在美国进攻拉卡前不久,俄罗斯和叙利亚军队发动了一场大规模进攻,以夺取反政府武装控制的阿勒颇东部地区。他们不顾国际法,以野蛮的攻势夺回了这座城市,把原本繁华的市场和医院夷为平地。
然而,从最终的结果来看,拉卡与这场进攻也没有什么不同:大量平民死亡,被炸成马蜂窝的公寓楼,被碎石瓦砾堵塞的街道,被夷为平地的整片社区。
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对拉卡发动的进攻初看完全符合战争法。一支由律师组成的队伍,就像仔细研究公司的最新合同一样,仔细审查每一个目标、每一场行动。在战斗中,联军指挥官斯蒂芬·汤森中将宣布:“我敢说任何人在战争史上都找不到比这次更精确的空战行动了。”
尽管人权活动人士坚称,联军本可以做更多来保护平民,但汤森是对的:美国没有像俄罗斯那样不加选择地轰炸平民。即使美国将整座城市夷为平地,在此过程中杀死了数千人,却没有明显地触犯人道战争的任何条款。
2016年夏天,叙利亚北部的河边小村庄托卡尔(Tokhar)的居民每晚聚集在社区边缘的四栋房子里,希望借此躲避炮火和炸弹。这是距离前线最远的地方。一英里外,美国支持的部队正在那里与ISIS武装分子交战。每天晚上,一架无人机都会在托卡尔上空盘旋,拍摄村民们从分散的家园走到这些临时避难所的过程。地下室里挤满了农民、母亲、女学生和小孩子。
7月18日凌晨3点左右,房屋爆炸。浓烟覆盖了夜空,断壁残垣上散落着残肢,孩子们被埋在倒塌的墙下。
周围村庄的人们花了两周时间挖掘尸体。与此同时,联军宣布当晚在该地区摧毁了“9个ISIS战斗阵地、1个ISIS指挥控制中心和12辆ISIS战车”。最终,在许多平民死亡的报告浮出水面后,联军承认杀害了24名平民。
然而,当我和一名同事在突袭发生一年后访问那里时,我们记录了至少120名平民的死亡,并且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有ISIS成员出现在那四栋房子附近。一位母亲告诉我,一些年幼的孩子失踪了,尸体都没能找到。
美国海军陆战队少校阿德里安·加洛韦说:“为了遵守《武装冲突法》的所有原则,我们在目标确定过程中采取了万全的措施”。这部法典的精髓是军队不能故意杀害平民。
的确,那天晚上,指挥系统中没有人想要屠杀平民,无论是飞行员、狙击手,还是律师。美国指出这一事实,称托卡尔事件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错误,但并不违法。然而,当涉及到个人的心态时,考虑主观动机是合理的,这就是法律概念中“犯罪意图”,但是在一个集体,如军队或国家上寻找主观意图,就有点奇怪了。
很明显,联军本可以预见其行动的结果:它已在该地区进行了数周的拍摄,这个村庄有平民居住的信息并不难收集。在联军打击ISIS的行动中,其轰炸决定往往基于对平民生活的错误假设;在摩苏尔,美军连续几个下午没能观察到平民在户外的情况后,就错误地将两户人家作为轰炸目标。
为了躲避炎热,伊拉克人民下午通常是不出门的,这场失败的侦查导致四人死亡。《武装冲突法》可以惩罚明明白白的错误,禁止故意杀人,但大多数美国战争都处于灰色地带,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法律本身非常模糊。
法典的第二个支柱是比例相称原则:如果国家的目标是军事目标,只要平民生命的损失可以换来比例相称的军事优势,那就可以杀死平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谁也不知道:怎么用人命来衡量“军事优势”?
在摩苏尔战役中,敌方狙击手爬上摩苏尔大学前工程学院院长穆罕默德·莱拉家的屋顶。据邻居说,他和妻子冲上楼,恳求他们离开。一瞬间,一枚弹头夷平了房屋,杀死了楼下的狙击手,莱拉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女儿全都被炸死了。
两名死去的敌人和一个死去的家庭怎么权衡,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大多数公约都会认为这种杀戮是合法的。拉卡的大部分破坏都是遵循莱拉家庭的例子:按相称的比例击杀。
美国官员很快指出,ISIS应该承担相当大的责任:武装分子不是故意分散在学校和公寓楼各处,就是住在平民之中。
然而,这并不能免除美国的责任。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冲突期间,反叛乱主义(美国发起的,采取民事和军事行动,遏制叛乱并解决其根源的思想)盛行时,美国军队也试图通过插入人口中心来赢得“民心”。
对于阿富汗人来说,没有什么能比一队米色的悍马装甲车蜿蜒穿过拥挤的街市更让人胆战心惊的了。如果一个人肉炸弹袭击了悍马车,美国人会理所当然地谴责他对周围平民的漠视——即使这个人肉炸弹背后也有法律力量,比例相称原则的支撑。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一名年轻的英国军官将步枪瞄准器对准目标,结果发现,“向一个浑然不知的无罪之人背后开枪是一件痛苦的事”。那个被瞄准的人,就是乔治·华盛顿。
美国军事行为中的矛盾并没有被忽视。人权组织经常指责美国犯下战争罪,包括在拉卡战役中。不过,在几乎每一个案件里,美国都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辩护。
争议点不在于美国是否杀害了平民,而在于对法律的解释:美国对故意性和比例相称性的解释比大多数人权团体的解释要宽松得多。在这些死亡事件发生后,没有一个独立的仲裁者来裁决美国的行动,只有战败的军队才会被拖上国际法庭。五角大楼只能自己审判自己,而且,毫不意外地,总是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判决。
法律的含糊不清使得美国可以将托卡尔这样的暴行定性为事故,即使致命的后果是可预见的,因此也是可避免的。
拉卡有多少平民的死亡是可以避免的?在托卡尔,重新收集证据是可能的,但往往没有这么做。目标确定过程缺乏透明度,军方拥有最终决定权。
然而,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我们直观地知道,武装部队除了蹂躏平民以外,其实还有其他选择。当美军在公寓楼的屋顶上面对两个ISIS武装分子时,他们可以调用一枚500磅重的激光制导炸弹,或者他们可以冒着敌人的火力,徒步接近敌人,通过老式的进展搏斗来确保大楼的安全。
在过去,军队有时会选择困难的路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盟军中的法国空军对维希(维希是法国领土的一部分)地区执行轰炸时,他们以较低的高度飞行,以免打击到平民,尽管这会增加了他们被击落的风险。然
而,对于美国军方来说,这些规定带来的风险太大。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武装部队要不要以增加自身风险为代价去减轻对平民的伤害。因此,瑞尼克认为,完全通过无人机发动的战争,指向了“在战场上合法行为与道德标准之间的严重不和谐”。
今天的美国军队不怎么提到勇气这种古老的军事美德了,因为远程作战不再需要太大的勇气。然而,从历史上看,这概念是优秀士兵的核心理念,甚至缺乏勇气的武器或战术都会遭到军队的反对。瑞尼克写道,在19世纪10年代,当飞机第一次进入现代军火库时,战斗机飞行员参与的空中缠斗让人想起中世纪决斗的英勇。但是像迫击炮和空中轰炸这样的远距离战术与英勇毫无关系。
参加过一战的一名飞行员回忆说,“当你坐在泥泞的战壕里,一个跟你无缘无故的敌人在五英里外放出一炮,把你炸成碎片,这毫无意义,”他总结道,“那不叫战斗,那叫谋杀。而且是愚蠢、残酷、不光彩的。”
一位二战时期的英国飞行员写道:“我是个战斗机飞行员,从来没有当过轰炸机飞行员,为此我感谢上帝。如果我是一名轰炸机飞行员,我不相信自己会服从命令。从高空向德国城市投放炸弹不会给我带来任何成就感。”
尽管狙击造成的破坏要小得多,但它长期以来一直引起类似的不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英国准将谴责这种行为是“冷血的谋杀行为,对最冷酷无情的人来说都是很可怕的,除了最变态的人之外,所有人都会感到厌恶”。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一名年轻的英国军官将步枪瞄准器对准目标,结果发现,“向一个浑然不知的无罪之人背后开枪是一件痛苦的事”。那个被瞄准的人,就是乔治·华盛顿。
2014年,传记电影《美国狙击手》(American Sniper)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大家很好奇电影中的这位传奇神枪手的故事是不是捏造的。但是,瑞尼克指出,没有人质疑狙击本身的道德合法性,这表明短兵相接的勇气已经不再是战场上的道德准则了。尽管他夸大了英勇在历史上的作用,但很明显,今天的美国军队竭尽全力避免风险,并且利用《武装冲突法》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一个强调勇气的军队可能会保护更多的平民,但也会使烈士名单变长,一旦这个名单进入美国,我们就得应付那些棘手的问题:那些美国人的死亡值得吗?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应该打仗吗?如果可以,能用不同的方式来作战吗?军方和人权组织似乎都不想面对这些问题。
反对战争法的人可能会说,叙利亚的废墟揭示了战争法的局限性:两支在完全不同的规范下作战的军队,在拉卡和阿勒颇取得了几乎相同的结果。捍卫战争法的人可能会反驳说,有这样的法律法规,即使有些模糊或过于宽松,也总比没有好。
也许这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对战争合法性的关注可能帮助人们逃避了对战争的负罪感。人权组织已经发现,美国在阿富汗犯下了数十起战争罪行,但大多数美国人的杀戮都是合法的:一名家庭主妇在离车队太近的地方徘徊,一名农民因错误的假设而被枪杀,一个家庭成为对称原则的受害者。美国人似乎只有在公然违反规则时,才会对战争产生负罪感;只要不违反规则,任何行为都是合理的,并且将永远合理。
也许只有当我们的海外战争受到民主约束时,我们才会把战争的开始和结束,而不仅仅是战争的行为,看作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如果阿富汗战争再持续20年,即使最终带来的痛苦,可能与为了取得决定性胜利而进行肆意屠杀一样大,但是会不会引起国内的反对令人怀疑。
美国不可能在不违反法律、不引起广泛反对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的屠杀,所以冲突一直处于低潮。美国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特殊的境地,它不能赢,也不能输。
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一些思想家拥护现实主义学说,这种学说直言不讳地指出,不应该把道德约束用在战场上。但这一学说给战场上很多可怕的、不必要的杀戮提供了很好的借口。另一种方法是和平主义,它尽管有种种优点,却要求我们同时谴责暴政和反抗暴政的人。这就留下了“正义战争”的道德传统。正义战争坚持认为,战争是人类生存的必然,因此,我们所能期望的最好结果,就是规范战争的时间和方式。这就是战争法的基本思想。
尽管武装冲突不会很快消失,但我们不需要把战争局限在违反法律和战场规则的问题上。伊曼努尔·康德(德国启蒙时代著名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认为,即使我们永远不能消除战争,我们也应该本着消除战争的目标,设计我们的战争法律法规。
今天在美国,我们可以努力使五角大楼的决定不受国防承包商和其他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将发动战争的决定权重新交由民主控制。911事件后,国会通过了《军事力量使用授权》,自那以后,美国总统在没有正式声明或公开辩论的情况下,使用这一授权,为在14个国家进行的至少37项军事行动辩护,其中就包括美国在叙利亚的战争。
不管总统们引用这个授权是否合法,或者美国的军队有没有踏上叙利亚的土地,这些问题都不及美国可以在没有公开讨论和征询民意的前提下,擅自夷平一座外国城市这一问题来得严重。也许只有当我们的海外战争受到民主约束时,我们才会把战争的开始和结束,而不仅仅是战争的行为,看作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