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的长文,从现实和历史的原因,分析了为什么曾经的大英帝国,今天却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而且最近的一连串政治变动,也成了国际笑话。

当你接近贝尔顿大厦时,车道是倾斜的。当道路再次倾斜时,大厦金色的正面会在你面前升起。
穿过铺着大理石地板的大厅,来到装饰华丽的酒吧。早年的游客会欣赏原主人的女儿和一位黑人侍者的肖像。国家信托基金会(National Trust)的菲奥娜·霍尔说(国家信托基金会是一家遗产慈善机构,如今拥有这处房产),有一段时间,仆人们会通过一条隐蔽的过道,从厨房走进走出。
一段宏伟的楼梯最终通向一个屋顶圆顶,可以看到地平线以外的一片庄园。
这座田园诗般的豪宅,建于1680年代,就像还活在英国古装剧里,在国内外都很被看重。大厦位于林肯郡的位置,在另一个方面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英格兰的中心,在2016年决定性地投票支持脱欧的地区;在格兰瑟姆的郊区,一个典型的集镇;英国战后最重要的总理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出生地。
这个充满历史气息的地点,以前曾是一个以穿古代服装嫌疑人为主角的神秘谋杀案解谜晚会的举办地,现在是思考另一种神秘论的恰当场所。
是谁让英国变得当下这个德性了?
不要笑,受害者的状况已经很糟糕了。一个喜欢以冷静的常识和好脾气的稳定而自诩的国家,已经成为一个国际笑柄:在几个月内有三位首相,四位财政大臣和一连串辞职的部长,其中一些进进出出好几次了。
本杰明·迪斯雷利在1872年大言的宣称,“保守党的纲领是维护国家的宪法”。结果,最近一批贵党的领导人,却违反了他们自己的律令,排挤了官方监督者,不尊重议会,不遵守条约。
不仅仅是一个政党,或一个政府,而是英国本身似乎都有点要崩溃的意思。
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盟,在贝尔顿宫建成后不久被强化了的聪明,正在崩溃。自2008年金融崩盘以来,英国人的实际收入令人失望,随着经济落后于其他大多数富裕国家,还会有更多年的发展停滞。
9月不计后果的减税小型预算案(注,指特拉斯的短命预算案),有可能导致致命一击。英镑暴跌,市场对英国主权债务施加了新的溢价——白痴溢价,英格兰银行只好直接出面拯救政府。
今天,英国经济正在进入衰退期,通胀率很高,罢工正在扰乱铁路、学校甚至医院。国家卫生服务(NHS),英国最珍视的机构,正在倒下:数百万人在医院里等待治疗,救护车的数量非常稀少。
在格兰瑟姆,这个有着整齐的红砖排屋、半木结构的酒馆和45000名居民的小镇,萎靡不振正在困难重重的的暗影中伸出头来。在NHS人员短缺的情况下,当地削减了紧急护理服务,引起了一阵骚动。
经营当地食品银行(注,西方国家一种慈善机构)的布莱恩·汉伯里说,尿布和玉米片需求量比去年增加了50%,而且随着取暖费的增加,预料需求量将剧增。
债务解决方案公司PayPlan的瑞秋·达菲是当地最大的雇主之一,她预测全国范围内对债务帮助的需求即将爆发,因为固定利率抵押贷款交易即将结束,人们已经感到压力。
至于特拉斯的减税小型预算案,格兰瑟姆保守党俱乐部的乔纳森·卡梅克感叹道:“简直是一场灾难”。
事已到此

谁干的?
在这场灾难中,嫌疑人很多。有些显而易见的,有些则潜伏在历史的阴影中,悄悄下毒而不是一击毙命。有几个是局外人,但就像许多最诡异的谜案一样,大多数都在屋内。
首先,记忆力好的英国人可能会发现一个熟悉的情况:一个已经衰弱的老年政府。
10月,议会送给即将辞职的特拉斯一句话,“首相不能躲在办公桌下”。这让人回想起了1997年至2010年工党政府死亡漩涡中的不朽名句。
然后,财政大臣把首相的随从称为“地狱力量”,内政部长的丈夫把色情服务的开销算进公费。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1979年开始的保守党统治进入尾声,一批议员被抓住,裤子都脱了,或者把他们的舒伸进了钱柜(注,这是指各种丑闻)。
这简直是另一场耻辱的接力。
英国似乎陷入了一个超龄政府的厄运循环中。这些政府刚开始会有一两届富有魅力的领导和改革主义的活力,然后就变得人才匮乏,在自己的错误中沉沦,被后座的叛乱所困扰(注,后座一般是指没有在内阁任职的议员);还在台上但权力迅速消逝,最终在投票中被击溃。有罪的政党需要经过几个议会任期才能恢复。
从反对党的角度来看,工党和保守党都坚定地从失败中吸取了错误的教训,然后再回头去找寻正确的教训。在一个有两个大党的体系中,任何一方失去理智都是危险的。如果两个政党同时失去理智,就像最近在保守党人的骚动中,工党却正好由杰里米·科尔宾领导一样——一个强硬的左派反叛者,同样是一场灾难。
乔治·奥威尔在谈到英国时写道:“一个由错误成员控制的家庭”。然而,衰老的政府重复循环本身,并不能解释英国的困境。以前的那些类似政府从来没有达到现在的混乱程度,所以这个国家这次还受到了其他东西的冲击,喷涌而出的政策和领导人的顺序,类似于人类的逆生长:从没有主见的大卫·卡梅伦,到神神叨叨的特蕾莎·梅,再到厚脸皮的鲍里斯·约翰逊,然后是现代史上最糟糕的首相特拉斯女士。
伦敦玛丽皇后大学的菲利普·考利说,在过去的日子里,在其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瑞希·苏纳克最多也就是个初级财政部长,而不是新首相。
政治暴力已经在英国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最明目张胆的就是英国脱欧,在公投中得到了52%的支持。执政超过十年的党派,必然会让人才枯竭,水准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当支持英国脱欧成为执政的先决条件时,保守党的大部分优良品质都被倒进了下水道,结果是被一些骗子和怪胎所统治。
约翰逊的脱欧阴谋,使他进入唐宁街;竞选活动促成的部落主义,使他呆在那里的时间比应该的要长得多。英国脱欧毁掉了保守党,但从表面的意义上讲,保守党反而是获胜的一方。
英国脱欧还使英国政治中的谎言制度化,因为英国脱欧派的不诚实承诺,转变成了他们正在履行承诺的假象,其实都是装蒜。
“没有什么变化,”格兰瑟姆的卡梅克黯然说道。“生活只是在继续。”
但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变得更糟了。投资减少了,通胀率比欧盟要高。劳动力,不管是熟练的还是不熟练的,都很稀缺。
农民因为缺少工人而失去了农作物。全国农民联盟的约翰娜·穆森说,在林肯郡,郁金香种植者更忧心。县里的出口已经下降,因为在整个英国,英国脱欧引起的繁文缛节,导致一些企业放弃了欧洲市场。
1975年,英国曾就其与欧洲的关系举行了另一次公投。亲欧的政治家罗伊·詹金斯预言,如果英国脱了,将把自己落入“褪色国家的老人院”,听起来让人欣慰,至少不是去了疯人院。
这个判断看起来是有预见性的,现在英国经济陷入困境,国际声誉一落千丈,而英国脱欧时,本来说要避免这样的未来。
然而,正如任何谋杀案解谜爱好者所知,最明显的嫌疑人很少真的是。在英国衰落的奇特案例中,脱欧既是一种武器,也是最终的背锅侠。
历史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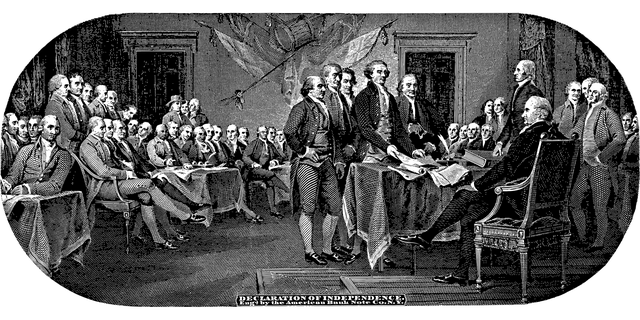
脱欧决定背后的许多因素,也对其他国家造成了困扰。大西洋两岸的许多人,都渴望为复杂的问题找到简单的答案,而民粹主义者跳出来说,“我知道我知道”。
人们对主流政党的信心已经减弱,即使对政府的期望值已经更高。
政治和娱乐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在英国,人们不愿意把事情看得太严重,而且对那些对传统观念嗤之以鼻的聪明人和怪人感到软弱无力。如果在他们的轻率背后还有点真货,在华丽的外表下有一点自律,那么这种伤害就会小一些。
全球研究公司益普索的老板本·佩奇,指出了他所谓的“失去的未来”,这种情况在整个西方国家都很常见,但在英国很严重。
佩奇指出,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只有12%的英国人认为年轻人生活质量会比他们的父母差。现在这个数字是41%。和其他地方一样,人们担心移民问题,并感受到全球化的威胁。
所有这些都使英国的困境,看起来不是内部问题,而是全球更大范围内民主被破坏的一部分。
但在英国历史的阁楼上,还潜藏着其他可能的嫌疑人。有一个人就在贝尔顿宫的路上长大,玛格丽特·罗伯茨,即后来的撒切尔夫人。她出生的格兰瑟姆杂货店,现在是一家脊椎按摩和美容院。
今年早些时候竖立的撒切尔雕像,很快就被人用鸡蛋砸坏了。她的传奇故事或者说阴影,仍然笼罩着这个国家,特别是她的保守党。
撒切尔的11年统治,是谨慎、耐心、运气和大胆的结合。但在一些保守党人中,人们常常误以为她没事就狂躁的减税、挑衅、抨击工会,对布鲁塞尔大喊“不,不,不 ”。在她领导下爆发的有关欧洲的争论,一直持续到2016年的公投。
对一些人来说,她留下了一种预见,即如果经济政策不痛不痒,就没有用。她下台,开始在保守党内培养了一种延续至今的党内放血的传统。为了讨好保守党成员,特拉斯甚至似乎在模仿撒切尔的衣着,毕竟把她送进了唐宁街的,只有81326人。
再深入了解一下过去,更多的证据就会浮出水面。
例如,回顾一下贝尔顿宫沙龙里的那幅画,画中的女孩和她的黑人随从,可能是一个奴隶。她的家族,即布朗罗家族,与加勒比海种植园和东印度公司都有联系,这有助于解释房子里华丽的亚洲瓷器收藏。
一个合理的理论认为,英国前帝国留下的更全面的遗产,是一种无法满足的期望和对英国世界地位的宏伟错觉,这错觉相当要命。
《帝国之地》的作者萨特南·桑格拉(Sathnam Sanghera)认为,“英国脱欧背后的原罪是帝国主义”,这是一本关于帝国主义影响的出色书籍。丧失帝国的情况,可能使精神上的打击加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战争期间,至少在大众的想像中,英国是在高贵的独自抵抗纳粹进攻。
之后,英国开始发现自己被昔日的敌人削弱了,被打垮了,被超越了,于是养成了伟大和怨妇交织的感觉,被幽灵般的入侵幻觉困扰着。正如爱尔兰作家芬丹·奥图尔(Fintan O’Toole)所调侃的那样,“英国从未摆脱赢得战争的命运”。在他看来,英国脱欧是“帝国主义英格兰的最后一搏”。
也许不一定是最后一次。
即使是现在,你也能从一些英国政客对欧盟谈判代表或国际债券市场的谈话中,听到帝国式傲慢的回声,仿佛对方是地中海小酒馆的服务员,只要你足够大声地重复自己,他们就会服从。
英国在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疗保健或军队(或足球队)的空洞吹嘘中游荡,在一种纯粹的主权追求中游荡。但是在气候变化、大流行病和进口天然气的时代,这种纯粹主权已经见鬼去了。
桑格拉认为,“除非我们正视我们的历史,否则英国将继续运转不灵。” 根据这种逻辑,英国的崩跌将是一种因果报应。
18世纪的祸根

也许上面说的都对。
然而,帝国主义、伟大和所有这些,一直以来都是精英们的心事,大众没有那么关心。伦敦国王学院的弗农·博格达诺在富有启发性的新书《自由英国的奇特生存》中,引用了1951年对英国人进行的一项调查,当时帝国刚刚开始消失。
结果,一半的受访者说不出一个殖民地的名字(其中有一个人说是林肯郡)。
对于一个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统治着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国家来说,这显得很奇怪,在现代英国,最成问题的可能不是像帝国的终结或英国脱欧这样的大断裂,而是不那么引人注目的一种长期心智漂移。
换句话说,不是极端,而是冷漠。
回想一下贝尔顿宫建成的年代。在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决和短暂的英联邦之后,君主制得到了恢复。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英国人很早就完成了他们的大革命。但后来又想多了一点,逐渐向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制迈进。
这种零敲碎打的渐近方式,一直是这个国家政治演变的特点。维多利亚时代《经济学家》杂志的伟大编辑沃尔特·巴盖特(Walter Bagehot),注意到英国人在棘手的宪法问题上妥协或回避的习惯。
他在谈到这些失误时写道:“半途而废的战线成为永久的限制,后世的人换了个地方去战斗。”
大坑经常就这样被留下了,其中之一是对英国行政部门模糊和薄弱的约束。正如保守党大佬海尔森勋爵在1976年警告的那样,一个在下议院拥有安全多数的政府,会有一种内在的“选举式独裁”的倾向性。
负责审查立法的上议院,整个就是一个漂亮的橡皮图章。在1999年的一项荒唐的幕后交易中,曾经主宰上议院的世袭贵族被驱逐,但其中92人除外。他们现在仍然在那里,当一个人去世时,另一个人被选出来代替他。
这就是议会上院的唯一选举。
很难看到许多其他国家会容忍这样的闹剧。同时,曾经被称为“好家伙”的政府领导理论,只是规范个人行为的君子协定,遇上了约翰逊什么用都没有。当政治暴民意识到法治只是是一种比谁更自信的把戏时,事实证明,糊弄几下就可以让各种监督变得儿戏。
或者考虑一下历届政府对权力下放的近视态度。布莱尔爵士的工党政府在创建苏格兰议会时,并没有完全预见到随后英国民族主义的激增,同样也没有预见到,在爱丁堡上任后,精明的、支持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将如何同时享有权力的尊严和反对威斯敏斯特的光泽。
现在,脱欧正在肆意破坏联合王国,打掉了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支持,这两个地区都投票决定留在欧盟。
斯特拉思克莱德大学的约翰·柯蒂斯爵士说,苏格兰独立曾经是一个可进可退的命题,而现在已经成为英国和欧洲这两个竞争性联盟之间的选择。随着苏格兰民族党发誓要重新加入欧盟,一些曾经拒绝独立的苏格兰留欧派正在接受这一想法。
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的凯蒂·海沃德解释说,对北爱尔兰的一些人来说,仅仅是英国脱欧的事实,就使统一的爱尔兰变得更加可取,这个地区脱欧后的尴尬处境,使更多人认为统一的可能性比以前更大。
在整个英国,大多数人认为欧盟最终会解体。这倒不一定,不过有一天英国倒很有可能会意外地自我解体。
漂移和冷漠所破坏的,不仅仅是宪法和联合王国。
20世纪英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大卫·凯纳斯顿引用了西格蒙德·沃伯格爵士(Sir Siegmund Warburg)的话,这位出生于德国的银行家帮助重组了伦敦金融城(在英国脱欧之后,股票市场滑坡)。沃伯格厌恶英国人对“车到山前必有路(原文为,We’ll cross that bridge when we come to it,直译为,当我们走到那座桥时,我们会过桥”的喜爱)。
正如凯纳斯顿所观察到的,英国并不是一个“善于抓紧时间”的地方。
除了一些明显的、反常的例外(撒切尔与煤矿工人的斗争,以及对英国脱欧的不满),英国一般来说倾向于厌恶对抗,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这也许是内战的遗留问题。英国人更喜欢机敏的讽刺,并将平铺直叙的话语,用良好的礼仪进行包装。当陌生人踩到他们的脚时,英国人有一种古板的道歉本能。
凯纳斯顿说,除了这种胆怯,还有一种“深染的反智经验主义”,以及一种“在问题出现时务实地解决问题,而不是事先寻找麻烦”的倾向。
这种冷漠是有代价的,尤其是有了一个缺乏动力的经济共谋。
考虑一下冰冷的规划制度,或者更古老的问题:不平等的教育系统。后者产生了一个狭窄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被少数私立学校的校友所支配。
英国脱欧和小型预算案,都可以追溯到伊顿公学的操场上,约翰逊、卡梅伦(他搞砸了公投)和夸西·夸滕(曾短暂担任过财政部长),都曾在那里学习。
这个事情不太显眼,但至少同样具有破坏性的,是这个国家漫长的教育遗留问题。
英国最近在国际教育排名中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英格兰,四分之一左右的11岁儿童无法达到预期的阅读水平。未参加工作、教育或培训的十几岁男孩的比例,高于其他大多数富裕国家。
至于那些留在教室里的人:“学校和大学所教的大部分内容……似乎并不是为”在余下的日子里去工作”做最适当的准备。这是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说的话,雇主们在2022年又提出了类似的抱怨。
在一个后帝国时代、后工业时代、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中,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技能短缺和与其他先进经济体的长期生产力差距。布莱尔和戈登·布朗爵士领导下的镀金岁月,掩盖了这些缺点。直到崩溃时,人们才发现他们监督下的繁荣,过度依赖金融服务和债务。
利用撒切尔主义经济学的成果,来给一个更慷慨的国家提供资金,这似乎是一种政治灵丹妙药。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陷阱。在最友好的环境下,新工党留下了一些最困难的问题没有解决。大多数新工作都给了外国出生的工人。领取福利金的工作年龄成年人数量几乎没有变化。
工业革命的摇篮,还没有在21世纪的经济中找到一个安全的位置,也没有弄清楚如何可持续地支付英国人所期望的那种公共服务。如果说在英国经济崩溃的问题上,撒切尔是事实面前的帮凶,那么布莱尔也是。
乡间别墅的红鲱鱼
在楼上楼下的英国乡间别墅愿景中,国家是一个阶级博物馆,领主们在勘察他们的土地,而仆人们则在楼梯下窜来窜去,就像他们曾经在贝尔顿宫做的那样。
很出名,迪斯雷利曾写道:“两个国家”,富人和穷人,就像“不同星球的居民”一样不同。尤其是在英国,确实是一个阶级森严的地方,居民仍然根据口音、鞋子和发型,判断对方的背景。
太多处于底层的人看不到向上的道路。一些在顶层的人仍然得益于不应有的尊重。政治家们常常赞同这种二元观点,认为政府的工作就是压榨富人,安慰穷人,反过来也一样。
但迪斯雷利的提法,对于21世纪的英国来说太过粗糙。经过几代人的磨合,英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完全贫穷但绝不富有的国家。相反,他们“勉强过得去”,正如上一任首相梅所描述的那样。
以格兰瑟姆为例,这个选区2020年的平均收入为25,600英镑(32,900美元),略低于全国中位数。今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英国的人均GDP将比美国低25%以上。食物银行的汉伯里说,在生活成本的挤压下,不仅依赖福利的家庭,而且护士和教师都陷入了困境,“人们生活在如此接近边缘的地方”。
格兰瑟姆低矮的高街后面,有一座可爱的中世纪教堂,圣伍尔夫拉姆教堂的斯图尔特-克拉杜克神父说,这里到伦敦只有70分钟的火车车程,但威斯敏斯特的权力似乎很遥远。
他说,林肯郡感觉像是一个“被遗忘的郡”。当
地议会的领导凯勒姆·库克说,离开去上大学的年轻人往往不会再回来。地区不平等是另一个古老而艰难的问题,历届英国政府都只是不温不火地处理这个问题,看着伦敦吸纳人才和资本,而其他地方则落在后面。
漂移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或者,换一种说法,渐进主义。奥威尔在1947年写道,“英国人的一个高度原创的品质”,“就是他们不互相残杀的习惯”。通过慢慢扩大选举权并将劳工运动纳入民主政治,英国在19和20世纪避免了欧洲大陆式的极端主义。
博格达诺说,当自由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在欧洲其他地方灭亡时,却在英国幸存下来。与法国或意大利等极右势力重新抬头的地方相比,或者与超极化的美国相比,英国的自由主义仍然是健康的。特拉斯在唐宁街的任期是不光彩的,但博格达诺指出,她被悄悄地、有效地免职,没有发生骚乱或大惊小怪。
看上去,有缺陷的议会制度最后还是起了作用。
因此,漂移可以是良性的。但也可以把你带入死胡同,或者掉入悬崖。在英国,导致了经济上的平庸和不满,这反过来又促成了英国脱欧的大呼小叫和小型预算那种绝望而神奇的想法。
衰老的政府、自残的伤口、帝国的反击、腐蚀性的全球趋势、过去领导人的幽灵,这些都是帮凶。但是,英国灾难的主谋并没有明目张胆的呆在犯罪现场,而是需要写出一本研究报告。
说到底,英国还不够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