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Wendell Steavenson代表经济学人的1843杂志采访了一家在马里乌波尔被袭击后,往东逃向俄罗斯占领的顿涅茨克地区的乌克兰人。他们在马里乌波尔坚持了一个月,在被炸伤后逃离,他们经历了俄罗斯人的审查和冷眼,但也被俄罗斯的医院救治。最终他们在志愿者的帮助下成功进入格鲁吉亚,并开始考虑下一步。

2月23日,娜塔莉亚·巴拉巴斯从银行取出1000美元现金,准备去伊斯坦布尔度假。第二天枪声响起时,她和她的家人并不特别担心。俄罗斯和乌克兰自2014年以来一直在乌克兰东部交战,娜塔莉亚居住的马里乌波尔的人们已经习惯了砰砰的爆炸声:前线离这里只有10公里。
娜塔莉亚和她的家人,认为这种噪音预示着敌对行动的又一次爆发。娜塔莉亚24岁的儿子沃瓦问他们是否应该购买额外的食物。娜塔莉亚告诉他,他们还有很多。
一周后,轰炸越来越近,越来越激烈。3月2日晚上,电、暖气和水都停了。没有互联网、移动电话和电视信号。娜塔莉亚说:“就像是生活在一个鸡蛋壳里。”
这家人把底层公寓的窗户用木板封起来。他们从废弃的商店收集食物并分发给邻居。他们设法用井水装满了一个大水箱,家里的每个人都停止了洗澡,以使水能用更长时间。12岁的纳西娅和她的猫一起蜷缩在床垫上,几乎一动不动。
娜塔莉亚说:“晚上是一片漆黑,没有灯光,白天在被涂黑的窗户后面也是漆黑的。”
晚上的温度低于零度,他们一直穿着套头衫和大衣。
战争初期,乌克兰士兵进入街区五楼的一个公寓,把阳台作为射击阵地。居民们恳求他们不要这样做,但士兵们没有理会他们。射击不可避免地引来了俄国人的炮火。街区被击中,开始从屋顶向下燃烧。当地人与火焰搏斗了几个小时。由于奇迹般的干预,风把火从巴拉巴斯的公寓吹走了。战斗越来越近。战斗机在头顶呼啸,空气中充满了火花和烟雾。
巴拉巴斯一家曾经在马里乌波尔过着幸福和富裕的生活。娜塔莉亚和她的丈夫罗玛在亚速钢铁厂工作,厂里有近1.1万名员工。沃瓦正在完成冶金学学位,并在工厂工作以攒钱买房。年幼的孩子科斯塔亚和纳西娅还在上学。
自2014年以来,顿涅茨克省被一分为二,当时独立广场的抗议活动推翻了亲俄罗斯的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俄罗斯支持一群分离主义分子,他们宣布自己为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并对乌克兰国家发起了战争。俄罗斯利用其正规军支持叛乱分子。
马里乌波尔仍在乌克兰控制之下,但当地的许多人对推翻亚努科维奇的革命没什么想法,也不喜欢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娜塔莉亚说:“我们想在他们头上泼一大碗水,这样他们就会回家了。”
与马里乌波尔的大多数人一样,巴拉巴斯一家讲俄语,并有俄罗斯朋友。他们对战斗造成的分裂感到沮丧。罗玛说:“家庭被拆散了。邻居们打了起来。”
他们不想选择立场。娜塔莉亚多次对我说:“我们不搞政治。”
3月15日,战争开始近三周后,沃瓦设法拿到了一台收音机,一家人了解了更多发生的事情。俄罗斯电台只是在冗长的音乐会广播之间简短地提到乌克兰的“特别行动”。乌克兰电台建议马里乌波尔的居民撤离,但没有提供实际信息。一些试图开车出去的邻居报告说,他们被乌克兰检查站挡了回来。
巴拉巴斯一家耽搁了太长时间。这座城市被包围了。沃瓦说:“起初,我的父母说,等俄国人进城后,我们再担心这个问题。”
他对他们的愚昧无知翻了个白眼,“当俄国人进城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会一直呆到他们轰炸我们的街区’。然后当我们的街道被击中时,他们说,‘我们会一直呆到我们的楼房被击中’。事实上,我们一直呆到几乎被摧毁。
”娜塔莉亚现在倾向于同意这句话:“聪明的人上了车,立即离开。我们并不聪明。”
娜塔莉亚用简洁、准确的句子,实事求是地描述了在马里乌波尔的那一个月的恐怖经历。她不时地停顿下来,吸一口气,半叹气,半调整,然后继续。她给我画了一张城市地图来说明这些事件。当我们说到3月16日的时候,地图已经变成了一团蓝色的笔迹。标志着她的公寓的那个小圆圈就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前线之间。
俄罗斯军队已经占领了隔壁街道的住宅区,科斯塔亚的女友也叫纳西娅,就住在那里。一位邻居告诉他们,她的楼房着火了,这对年轻恋人就去调查。俄罗斯士兵被安排在每个入口处。一名士兵检查了科斯塔亚的手臂上是否有亲乌克兰的纹身。
起初,16岁的科斯塔亚很害怕,但随着他们交谈起来,士兵们看起来像普通人。他们告诉他,大巴将向东疏散人们。科斯特亚说,他家自己有汽车。士兵们告诉他要避开大路,因为那里是个射击场。要尽快离开,一个人说,“今晚将是地狱”。
娜塔莉亚说,在轰鸣声之前,“通常会有一声很长的声音,peeee-ow,所以你还有点时间躲避。但这一次只有一声巨响”。
当一家人在收拾汽车时,一枚炮弹在院子里爆炸了。沃瓦被抛到了地上;他感觉不到自己的左腿了。当他抬起头时,他看到父亲一瘸一拐,但仍然站着。弹片将科斯塔亚的脸撕开,他的食指被一丝丝的皮肤挂住。
娜塔莉亚的姐姐正弯腰抱着她的儿子瓦迪姆,拼命地试图阻止从他脖子上喷出的血泉。沃瓦可以从他变木然的眼睛里看出他已经死了。

那晚的细节杂乱无章,血肉模糊。科斯塔亚突然很热,很渴,哭着说他不想让他的女朋友看到他这样的脸。罗玛把行李扔出车外,把科斯塔亚放在后座上,然后开车去医院,因为他自己的大腿也在流血,他拼命地在散落着瓦砾的街道上穿梭。
医院没有自来水和暖气,没有麻醉剂和药品,也没有外科医生,只有一个疲惫不堪的初级医生。娜塔莉亚从一堆废弃的衣服中偷了一条脏兮兮、沾满血迹的毯子,裹在瑟瑟发抖的科斯塔亚身上。医生告诉他们,最好把弹片留在沃瓦的膝盖后面。他把一叠绷带塞进罗玛大腿上的洞里,并告诉他们要用消毒剂保持伤口的清洁。
娜塔莉亚告诉他:“我们没有消毒剂。”
“用伏特加。”
“我们没有伏特加。”
他说:“那你可以用尿。”
娜塔莉亚不记得他们是怎么回到家的。全家都躺在同一个房间里,受伤了,浑身发抖,很冷。没有人睡觉。正如俄罗斯士兵所说的那样,炮击整晚都很猛烈;墙壁摇晃,石膏粉尘在空气中弥漫。
第二天早上,在黎明之前,他们终于离开了。罗玛带着受伤的男孩们和科斯塔亚的女友纳西娅乘坐蓝色汽车;娜塔莉亚带着女儿和她85岁的母亲驾驶着棕色汽车,车窗都被炸坏了,一个轮胎也瘪了。
离开被围困的马里乌波尔有两条路线:向西穿过乌克兰防线,或向东穿过俄罗斯防线进入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这座城市的居民被封锁了消息,夹在两支军队之间,不得不根据运气来选择。根据俄罗斯士兵的建议,巴拉巴斯一家向东走。
在第一个俄罗斯检查站,部队挥手让罗玛和他受伤的儿子们通过,并通过无线电通知救护车来接应他们。娜塔莉亚被告知要等待并跟随一个巴士车队。两个小时后,当他们出发时,爆胎意味着她的汽车只能缓慢爬行,以至于她跟不上车队。趴在方向盘上,她开车穿过废墟城市的郊区,然后撞上了一个俄罗斯坦克纵队。领头的坦克炮手高兴地叫道:“你的车胎爆了!”
出发六个小时后,娜塔莉亚到达了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贝齐米纳村(Bezimenne,在俄语中意为“无名”)。娜塔莉亚看到了罗玛停放的汽车。士兵们告诉她,车上的人已经去了医院,但他们不知道在哪里。他们指给她看在一个所谓的过滤点外等待的汽车长龙,在那里官员们对难民进行面试和登记,然后他们可以向东走得更远。(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采用了类似的程序,以评估从德国战俘营回来的俄罗斯人的意识形态是否健全。)

娜塔莉亚沿着排队的汽车走了40分钟。有些人已经在那里等了三天了。在终点处搭起了一个巨大的帐篷,里面有桌子,难民们坐在那里接受采访,还有营地床,让其中一些人可以休息。
娜塔莉亚很绝望:没有许可证,她无法找到她的丈夫和儿子。她精疲力竭、浑身脏兮兮、冷冰冰的,被引导到一个为老人和有小孩的家庭提供庇护的大型石头建筑,但那里已经满了。娜塔莉亚倒下了,哭了起来。负责人说他们可以呆在走廊里。
一名士兵开车送她去修车胎。其他人给她倒了杯咖啡安慰她,给她饼干和三明治。他们帮她把美元换成卢布,她还有为度假提取的1000美元,并打电话到医院询问她的家人被带到了哪里。
娜塔莉亚说:“他们是穿着军装的乌克兰人。他们不是俄罗斯士兵。他们对我们没有侵略性,我们对他们也没有侵略性。”
收容所的一名士兵让她使用他的无线热点,她一个月来第一次上网。她的Viber(一种聊天软件)群组亮起了信息:你在哪里?你还好吗?其中一条来自莫斯科的表兄弟,自2014年以来,她几乎没有和他说过话。他在贝齐米纳村拥有一栋又大又空的房子。他说,一个邻居有钥匙。娜塔莉亚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这所房子有电,但没有暖气。娜塔莉亚为炉子劈柴,买了土豆和黄油,并设法与在不同医院的罗玛和她的儿子们取得联系。娜塔莉亚被告知至少一周内不会被叫去接受过滤面试,但顿涅茨克的士兵设法让她排在前列,这样她就能更快地找到她受伤的儿子。
在过滤点,士兵们搜查了她的汽车行李箱和引擎盖。穿着军装的人检查文件:他们登记了她的名字,检查了她的身份证,拍了一张正面和侧面的照片,并扫描了她的指纹。在另一张桌子上,她被要求解锁她的手机,然后一名男子阅读了她的电报信息、Viber聊天记录、脸书帖子和WhatsApp信息。
在划了40分钟后,另一名官员告诉他要快点。“要么拘留她,要么让她走!”
这名男子说他才不会听人催。他将她的手机连接到一台电脑上,下载了全部内容。
在旁边的桌子上,娜塔莉亚填写了一份长长的调查问卷:你是否见过乌克兰情报部门的任何成员?你有朋友或亲戚在乌克兰军队中吗?你的邻居中是否有人展示过乌克兰国旗?她说:“我对所有这些都回答说没有。”
这个过程大约花了三个小时。最后,娜塔莉亚收到了一张许可证。她被告知,从现在开始一切都会好起来。
自战争开始以来,已有600多万人逃离乌克兰。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其中大部分人去了西部,但约有150万人进入了俄罗斯(有人认为这被高估了)。许多向东逃亡的人来自被占领的领土。在战争的最初几周,有报道称俄罗斯人强迫人们登上疏散巴士,将他们运往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
那些想离开俄罗斯的人必须走800多公里到高加索地区,越过山脉进入格鲁吉亚,或者绕一个大圈到达波罗的海国家,或者穿越白俄罗斯到达波兰。社交媒体上的数字小道消息提供建议和援助。有些是由善良的俄罗斯人建立的。
玛莎·贝尔金娜一家三年前离开莫斯科,以逃避政府的压迫,并搬到了邻国格鲁吉亚。2月战争爆发后,贝尔金娜在电报上发起了第比利斯志愿者组织,帮助乌克兰人获得安全。组织为难民提供租赁房屋的住所,并分发食物和其他必需品。同样位于第比利斯的“帮助离开”组织在世界各地有450名志愿者,回答询问并协调疏散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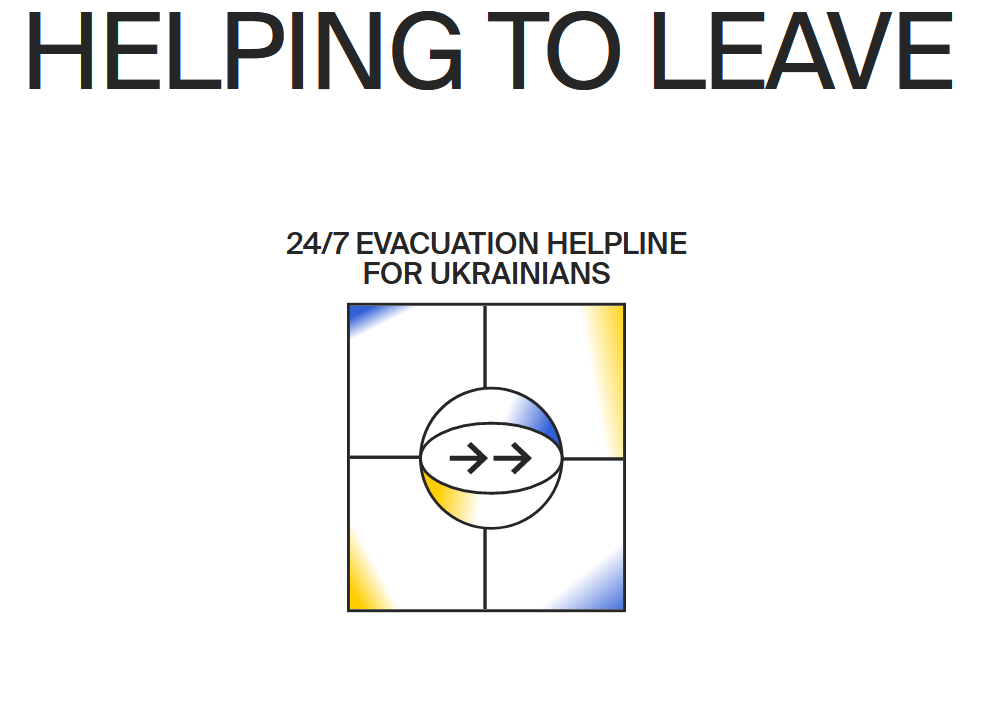
帮助离开组织和第比利斯志愿者组织都在顿涅茨克和俄罗斯的占领区内有网络,协助乌克兰难民。贝尔金娜说:“我们称他们为我们的雾中志愿者,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也没有人需要知道。我从未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她估计有1000名来自俄罗斯各地的人,自愿帮助乌克兰难民预订酒店房间,购买汽车票或找到一个住处。
这些志愿者对过滤过程有特别的洞见。虽然似乎没有什么标准程序。一些过滤点的工作人员是当地人,通常是曾经做过政府雇员或警察的中年妇女。在被占领的乌克兰部分地区,如赫尔松附近的南部地区,通常由俄罗斯士兵负责。所有这些都是由克格勃的后继组织FSB监督的。
官员们可能是友好的,也可能是冷漠的,或者是威胁性的。男子通常必须脱掉衣服,以防他们有亲乌克兰的纹身,或步枪的后坐力造成的伤痕。有些面谈是粗略的,有些则是恐吓性的。大多数乌克兰人没有受到伤害,但也有一些人被骚扰、殴打或失踪的故事。
居住在斯德哥尔摩的志愿者安娜为帮助离开组织管理一个团队(她不愿透露姓名),她说“不可能”说准有多少乌克兰人被逮捕,因为所有的信息都是传闻。她接到的一个电话是关于同一个村庄的200人,大部分是男性,他们被拘留了一个多月(他们后来被释放了)。
一旦通过过滤,乌克兰人要么留在顿涅茨克地区,要么登上巴士,跨越边境前往俄罗斯。在这里,他们可以住在亲戚家,租公寓,或者离开这个国家,如果他们有能力的话。那些发现自己在俄罗斯没有朋友、亲戚或钱的人只能听从制度的摆布,因为乌克兰银行卡在那里不起作用,而制裁意味着没有人可以从国外转移资金。
这些人被送上特殊列车,安娜说“我们称之为驱逐列车”, 他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目的地。
在俄罗斯的条件各不相同。有些人被安置在旅馆、疗养院或旧军营里。安娜知道,在俄罗斯中部的一个城市,有一个家庭住在一个漂亮的酒店里,食物很好,尽管工作人员因为他们的国籍而对他们很粗暴。其他人则被困在几乎没有任何设施的村庄里,靠喝稀饭和很稀的汤水为生。
有些人被送到最东边的海参崴或北极圈以北的摩尔曼斯克。
安娜说:“坏消息是,大多数人都留在俄罗斯。”
他们不仅因为缺钱,而且缺乏对其他路线的了解而被搁置。一些在俄罗斯的乌克兰人成为宣传的受害者:他们被警告说乌克兰人在欧洲受到虐待,同时被迫观看马里乌波尔恢复正常生活的画面。
同样的宣传,意味着许多俄罗斯人将所有乌克兰人视为敌人,即使克里姆林宫扭曲的叙述。将难民描述为泽连斯基总统的所谓纳粹政权的受害者。
当沃瓦到了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医院时,一名俄罗斯士兵看到他的亚速钢铁厂制服肩上的乌克兰国旗小补丁,愤怒地爆发了,大骂说自己是怎么与乌克兰人战斗了8年。沃瓦说这是一件工作服,并扯掉了补丁。这名士兵回答说:“如果我再看到你身上的乌克兰标志,我会让你把它吞下去。”
医院里的其他人则比较友好。一位老妇人送来了自制的薄煎饼,并不断说她为他感到非常抱歉。
在沃瓦的病房里康复的人中,有一个来自马里乌波尔的50多岁的男人,他因为一项他不愿透露的罪行,在监狱里呆了25年;一个顿涅茨克民兵的士兵,他无法相信马里乌波尔曾经是一个繁荣的城市(沃瓦形容他“迟钝地像块木头”);还有一个来自高加索山区的达吉斯坦的俄罗斯士兵。他为了钱接受了一份军队合同,但不明白为什么两个共同拥有一种宗教的俄语国家会发生战争。
他说:“这里发生了什么? 这就像一家子在打架。”
医生从沃瓦的膝盖上取出弹片,但他仍然无法行走。他担心会有永久性的神经损伤,于是联系了德国红十字会,希望能去德国接受更多治疗。许多从马里乌波尔向东逃亡的人在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等待,直到战斗停止,希望能返回家园。
娜塔莉亚和罗玛满足于呆在他们在贝齐米纳的表兄弟家。沃瓦说:“对我的父母来说,只要有一套房子,让他们可以住在里面。他们并不关心是在谁的领导下。但我想的是我如何能工作,关于未来。而在贝齐米纳没有未来。”
我问是什么说服了他的父母离开?沃瓦笑了起来:“谷歌是个好东西!”
娜塔莉亚听说了第比利斯志愿者组织的情况,并联系了贝尔金娜,想知道他们到了格鲁吉亚后可以住在哪里,以及乌克兰人是否真的可以得到免费医疗。贝尔金娜计算出哪个过滤点可能最快签发文件,并建议每个家庭成员清除手机中的联系人、图片和聊天记录。
他们准备好了在俄罗斯的亲戚的地址,以防他们被问及他们的目的地。在这种情况下,过滤点的官员没有做什么调查。贝尔金娜建议他们打受害者牌,所以娜塔莉亚告诉他们,她的儿子们需要在俄罗斯接受治疗,五分钟内,他们的证件就被盖上了章。
过境进入俄罗斯的时间很长:一家人被拦住了五个小时,他们的两辆车都被彻底搜查了。出发20小时后,巴拉巴斯一家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顿河畔罗斯托夫,这是一个靠近乌克兰边境的俄罗斯城市。他们精疲力竭,开着两辆汽车驶入一个加油站,弹孔依然清晰可见。

一个俄罗斯人注意到他们的马里乌波尔车牌,给他们买了一箱汽油和冰淇淋,并帮助他们找到了一家旅馆。他们的单人房间在一家廉价、破旧的旅馆里。娜塔莉亚说,“但它有热水!”
她回忆起来就笑了。巴拉巴斯家一个月来第一次洗澡,“黑水从我们身上流走了。”
这家人在俄罗斯遇到了不同的反应。有一个人,他华丽的汽车边上画有一个字母Z,直接对他们视而不见。另一个人把钱塞进科斯特亚的口袋。娜塔莉亚给几十个机械师打了电话,才找到一个同情他们的人,免费为他们的两辆车进行了维修。
4月初,这一家人又出发了。他们马不停蹄地开了两天,到达通往格鲁吉亚的唯一边境口岸。俄罗斯边防军抱怨他们没有正确的移民卡;格鲁吉亚边防军担心科斯塔亚和娜塔莉亚的母亲没有护照。
最终,全家人都被放行了。第比利斯志愿者组织的创始人贝尔金娜在另一边迎接他们。自战争开始以来,大约有2.5万名乌克兰人前往格鲁吉亚。
我在6月中旬见到巴拉巴斯一家时,他们已经在格鲁吉亚呆了两个月。科斯特亚的手在接受骨头移植手术,加固拇指后被包扎得像戴着手套,他已经失去了食指。他失明的左眼眼角微微下垂,下面的脸颊上有疤痕。他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还在成长中,但他带着一种与他稚嫩的外表不相符的稳重。
和他的父母一样,科斯塔亚在战前既不亲俄也不亲乌。入侵发生后,他仍坚持这一观点。“在战争中,你的思想会变窄。我们是为生存而战。我们并不关心我们是在俄罗斯国旗下还是乌克兰国旗下……我看到俄罗斯人帮助我们疏散。我曾认为俄罗斯人是好的。”
距离改变了这种看法,“自从我能够远离那段紧张的时期,我的思想又开阔了,我可以看到更大的画面。现在我想,俄罗斯人,该死的混蛋;乌克兰人,哇!他们是伟大的人。那些才是伟大的人。”

沃瓦的腿已经痊愈。一向勤奋的他最近参加了室内设计的在线课程,并参加了几次反战示威,在那里看到流亡的白俄罗斯人和俄罗斯人举着乌克兰国旗,他感到很欣慰。他说:“人们说俄罗斯人很坏,但俄罗斯人和我们一样都是普京的受害者。”
沃瓦认为,乌克兰人已经尽力保卫了马里乌波尔。
他的父母则更加含糊其辞。罗玛告诉我:“俄罗斯说他们正在从纳粹手中拯救乌克兰。乌克兰说他们在从俄罗斯的侵略中拯救马里乌波尔,但没有人想到人民。”
这家人正在决定是在加拿大还是在奥地利重新定居。沃瓦很纠结,他在基辅的女友希望他和她一起去德国。但他们都不希望回到马里乌波尔。他们的公寓现在是一片废墟,窗户上没有任何玻璃。据邻居们说,现在有一个俄罗斯人住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