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的Ronald Brownstein发表文章,分析了目前美国红蓝两方分歧的原因和后果。他引用的活动家迈克尔·波德霍泽认为,美国在历史上就有着根深蒂固的红蓝分裂,而上个世纪前半叶的团结才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情况。目前,由特朗普主义代表的红色阵营正在试图扩大影响,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并不认同他们的蓝色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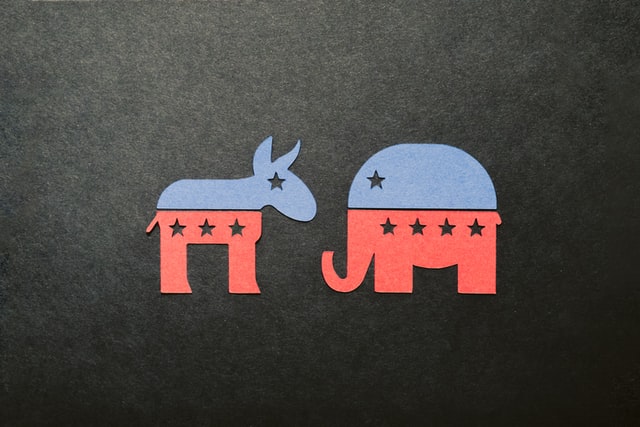
现在可能是停止谈论“红色”和“蓝色”美国的时候了。这是迈克尔·波德霍泽(Michael Podhorzer)的挑衅性结论,他是工会的长期政治战略家,也是研究选举的进步团体合作组织,分析家研究所(Analyst Institute)的主席。在他为一小组活动家撰写的私人通讯中,波德霍泽最近提出了一个详细的案例,即把这两个集团视为根本不同的国家,不安地共享同一个地理空间。
波德霍泽写道:“当我们考虑美国时,我们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就是把它想象成一个单一的国家,一个由红色和蓝色人群组成的交织混合体。但事实上,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国家。我们更像是一个由两个国家组成的联邦共和国,蓝色国家和红色国家。这不是一个比喻;它是一个地理和历史的现实。”
在波德霍泽看来,红州和蓝州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这代表着回归到美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的分离线。他写道,特朗普时代各州之间的差异“,在地理上和文化上都非常类似于联邦和南方联盟之间的分歧。而这些分界线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建国时确定的,当时奴隶州和自由州结成了一个不安的联盟,成为‘一个国家’”。
确切地说,波德霍泽并不是在预言另一场内战。但他警告说,对国家基本凝聚力的挑战,可能会在2020年代继续加大。与其他研究民主的分析家一样,他认为现在主导共和党的特朗普派,他称之为“MAGA运动”,相当于匈牙利和委内瑞拉等地的独裁政党。
这是一场多管齐下、从根本上反民主的运动,通过保守的媒体网络、福音派教会、富有的共和党捐助者、共和党民选官员、准军事的白人民族主义团体和大规模的公众追随者,建立了稳固的机构支持基础,而且决心将自己的政策和社会愿景强加给整个国家,无论是否得到多数人的支持。
波德霍泽认为:“对我们机构的结构性攻击为特朗普的参选铺平道路,并且将继续发展,不管有没有他掌舵。”

所有这些都助长了我所说的红蓝两州之间正在进行的“大分歧”。这种分歧本身对国家的凝聚力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凝聚只是一个暂时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清楚的是,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共和党希望利用他们在红州的选举优势、选举人团和参议院倾向的小州的偏见(注:由于无论每州人口多少,都同样有两位参议员),以及共和党在最高法院任命的多数派,将经济和社会模式强加给整个国家,无论是否得到大多数公众的支持。
正如在包括1月6日的叛乱、共和党2020年选举结果否认者正在竞选将使他们控制2024年选举机制的职位,以及最高法院系统地推进共和党议程等行动那样,2020年代的基本政治问题,仍然是多数统治和我们所知的民主是否能在这次进攻中幸存下来。
波德霍泽将现代美国的红蓝两色定义为,近年来一个党通常对州长和州立法机构拥有统一控制权的州。根据这一标准,有25个红州、17个蓝州和8个紫州,最后这些州的政府控制权通常是分裂的。
以此来衡量,红州容纳的合格投票人口略多(45%对39%),但蓝州对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更大。46%对40%。仅就其本身而言,蓝色国家将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中国。而红色国家将排名第三。
波德霍泽还提供了一个稍有不同的州分组,反映了最近的趋势,即弗吉尼亚州在总统一级的投票更像一个蓝州,而亚利桑那州和佐治亚州已经从红色转为紫色。将这三个州移入这些类别后,这两个“国家”在符合条件的投票年龄人口方面几乎相等,而蓝州在国内生产总值方面的优势大约翻了一番,蓝州贡献了48%,红州只有35%。
波德霍泽认为,红蓝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使10个紫色州(如果包括亚利桑那州和佐治亚州)“有能力”在总统和国会选举中“决定两个超级大国的价值观,既蓝红之间,哪一个将占上风”。这使得这个国家永远在刀刃上摇摆不定。
据他计算,在过去的三次总统选举中,这些紫色州中任何一党的总得票率,优势都不超过两个百分点。
红色国家和蓝色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分歧和对立,是21世纪美国的一个决定性特征。这与20世纪中期的趋势相反,当时的基本趋势是更加趋同。
这种融合的一个因素是通过法律学者所称的“权利革命”。这是国会和最高法院的一系列行动,主要始于20世纪60年代,这些行动加强了全国性权利的底线,减少了各州限制这些权利的能力。(这场革命的关键时刻包括《民权法案》和《投票权法案》的通过,以及最高法院推翻各州禁止避孕、异族通婚、堕胎以及后来对同性亲密关系和婚姻的裁决)。

同时,国家级投资的浪潮也缓和了地区差异,包括1930年代对农村电气化、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农业价格支持和社会保障的新政支出,以及为K-12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提供联邦援助的“伟大社会”计划,以及老人医疗保险和穷人的医疗补助。
这些投资(以及这两个时期的大规模国防开支),对历史上在公共服务和经济发展上花费不多的各州的影响,有助于从20世纪30年代到1980年左右,稳步缩小旧联邦各州与全国其他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
不过,这一进展在1980年后停止了,在接下来的30年里,这一差距基本没有变化。根据波德霍泽的计算,自2008年以来,位于红州中心的南部各州,在人均收入方面再次进一步落后于蓝州。
研究各州差异的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家杰克·格伦巴赫告诉我,红州作为一个群体,在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成果方面落后于蓝州,包括经济生产力、家庭收入、预期寿命以及阿片类药物危机和酗酒造成的“绝望之死”。
红州模式的捍卫者可以指出,其他指标显示这些地方的情况更有利。红州的住房通常更容易负担;正因为如此,无家可归者在许多蓝色大城市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红州的税收通常比蓝州的税收低,许多红州经历了强劲的就业增长(尽管这主要集中在其偏向蓝色的都市地区)。整个太阳地带(美国的南方各州,从加州到佛罗里达州)的红州是全国人口增长最快的一些州。
但最大的问题是,随着国家过渡到高生产力的21世纪信息经济,蓝州受益更多,而红州(除了参与这类经济的主要大都市中心)随着20世纪的强势产业,包括农业、制造业和化石燃料开采业的衰落,而受到影响。
根据波德霍泽的计算,现在蓝州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家庭收入中位数,都比红州高出25%以上。蓝州的贫困儿童比例比红州低20%以上,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工作家庭比例低近40%。健康结果也有差异。红州的枪支死亡人数几乎是蓝州的两倍,孕产妇死亡率也是如此。
蓝州的新冠疫苗接种率高出约20%,红州人均新冠死亡率高出约20%。蓝州的预期寿命(80.1岁)比红州(77.4岁)高出近3年。(在这些衡量标准中,紫色州恰好处于两者之间)。
与红州相比,蓝州在中小学教育方面的人均支出几乎高出50%。
所有蓝州都根据《平价医疗法案》扩大了医疗补助的使用范围,而红州总人口的约60%居住在拒绝这样做的州。
所有的蓝州都规定了高于联邦水平的7.25美元的最低工资,而只有约三分之一的红州居民生活在这样做的地方。
工作权法(Right to work law,禁止工会与雇主谈判合同的州法)在红州很普遍,而在蓝州则不存在,结果是后者的工会工人比例比前者高得多。
蓝州没有一个州的法律规定禁止在胎儿能存活前堕胎,而几乎所有的红州都准备在共和党任命的最高法院多数派推翻翻罗诉韦德案之后,限制堕胎权。
几乎所有的红州都通过了由全国步枪协会支持的“坚守阵地法”(stand your ground)的法律,为那些自认受到威胁而使用武器的人提供法律辩护,而蓝州没有这样做。
自2021年以来,红州在堕胎、课堂上对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的讨论,以及LGBTQ权利等问题上通过的大量社会保守派法律,正在扩大这种分歧。民主党控制的州都没有通过这些措施。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家莉莲娜·梅森告诉我,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19世纪末期到1965年间实施的各种种族隔离法律)的种族隔离经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点,以了解红州可能在多大程度上采取这种压制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运动,不是说他们真的会寻求恢复种族隔离,而是说他们认为“回到一个各州”的法律“彻底不同”,以至于形成一种国内种族隔离的情况,并没什么不好。
她说,随着两个区之间的距离扩大,“有各种真正深刻的破坏,社会性破坏的可能性,而且也不仅仅在我们的感觉和我们的意见上。”
对波德霍泽来说,越来越多的分割意味着在区别逐渐消失的时期之后,美国成立之初即存在的根本性差异正在重新浮现。他认为,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他所说的, “红色国家的一党统治”的回归。
通过一些复杂但有说服力的统计计算,他记录了吉姆·克劳时代的历史模式的回归,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政党(当时支持种族隔离主义的民主党,既现在的保守派共和党)歪曲了竞争环境,在红州取得了远远超过其民众支持水平的政治主导地位。
他认为,支撑这种优势的是,让在许多红州注册投票或投票变得更困难的法律,以及使共和党人几乎锁定了对许多州立法机构的无限期控制的严重选区划分。格伦巴赫在最近一篇分析各州民主趋势的论文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格伦巴赫说:“在这些州,由于这种民主倒退,形成了一种极度不公平的结果。”
波德霍泽的分析提出的核心问题是,美国将如何在两个相距如此遥远的部分同时运作。在我看来,历史提供了两种模式。
从19世纪90年代到60年代,在吉姆·克劳进行合法种族隔离的70年里,处于红色美国核心的南方各州的主要目标是防御。他们孜孜不倦地阻止联邦对州政府支持的种族隔离的干预,但并不寻求将其强加给这个地区以外的州。
相比之下,在内战前的最后几年,南方的政治取向是进攻性的。通过高院(1857年的德雷德·斯科特判决,确认了美国宪法中的公民权并不适用于非裔后裔,无论他们是否是奴隶)和国会(1854年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主要目的是取消了禁止一些南方州拥有奴隶的“密苏里妥协”),主要目的都是授权将奴隶制扩展到更多的领土和州。当时的南方各州不只是在其境内保护奴隶制,而是试图控制联邦政策,将他们的观点强加于全国更多地区,包括有可能推翻自由州对奴隶制的禁止规定。
特朗普时代的共和党人,在整个红州施行他们占多数的白人和基督教联盟的政策优先事项,似乎不太可能仅仅满足于在他们现在控制的地方制定规则。
像梅森和格伦巴赫一样,波德霍泽认为,MAGA运动的长期目标是在足够多的州倾斜选举规则,使民主党人几乎无法赢得国会或白宫。然后,在共和党任命的最高法院多数法官的支持下,共和党人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强加红州的价值观和计划,即使大多数美国人反对这些价值观和计划。
波德霍泽写道:“MAGA运动并没有止步于它已经控制的州的边界。它试图通过任何可能的手段,征服尽可能多的领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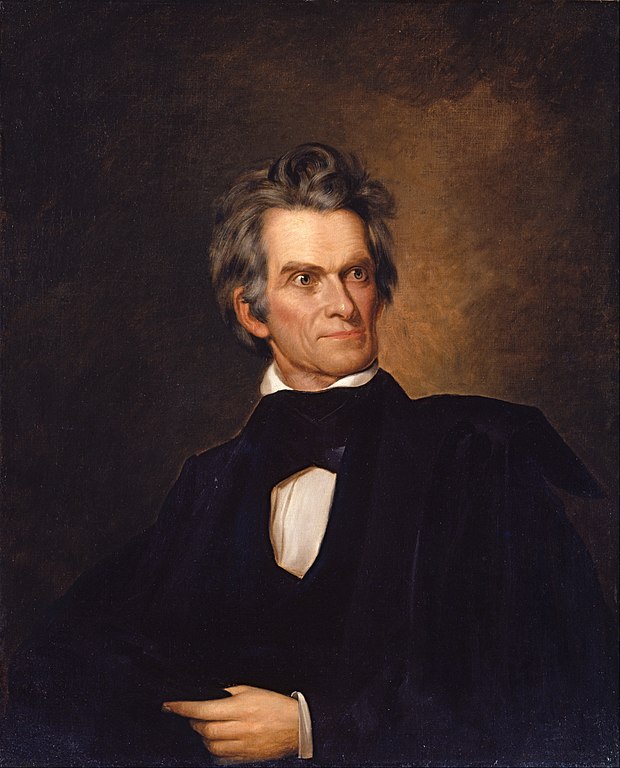
换句话说,特朗普模式更像是1850年的南方而不是1950年的南方,更像是约翰·卡尔霍恩(美国前副总统,坚决维护奴隶制,支持州权,小政府等措施,在参议院时致力于将奴隶制西扩)而不是理查德·拉塞尔(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支持种族隔离制度,反对1964年的民权法案)。
一些红州的共和党人甚至在隐约呼应卡尔霍恩,承诺废除,也就是藐视他们不同意的联邦法律。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注定要像19世纪50年代后那样再次相互争斗。但这确实意味着,2020年代可能会给国家的基本稳定,带来自那些黑暗和动荡年代以来的最大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