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佐溪
来到美国的36年间,傅丹灵先后读取了英语文学的硕士和读写教育的博士,成为了佛罗里达大学教育学院的终身教授。在传授读写教育方法的同时,她也将研究视角投向了“移二代”的英语学习,和公立学校的老师一起探索“边缘群体”的英语读写。
疫情之下,潜藏在美国教育系统中的问题正在放大。傅丹灵直言,当下是她“对美国教育和政治最失望”的时刻。

而通过她本人的经历,可以看到一个“边缘人”如何从彷徨不定到自我觉醒,这对当下的华人移民群体,尤其是“移二代”的身份认同依然有着观照意义。
一个“外来者”的自我觉醒
傅丹灵从小就爱看童话故事。灰姑娘、小红帽、青蛙王子、火柴姑娘、丑小鸭这些西方儿童文学开启了她对遥远国度的向往。成长过程中,她从未停止过阅读,以及对西方世界的想象。
十几岁时,傅丹灵下乡。临行前,她把阁楼里的书都装进了箱子。在农场的三年多里,她在农忙后的田野间,在雨雪纷飞的夜晚,借着一盏微弱的煤油灯,逐字逐句饱览苏联、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的文学译著,在书本里游历了各国。
一个农民曾对她说:“丹灵,即使你今天死了,也不用后悔,因为关于这个世界,你已经知道了那么多。” 这让她感到无比富有。
几年后,傅丹灵考取南京大学,选择了英语专业。第一次看到原版英文著作,她无比激动,自此沉浸在了英国和美国文学中,那里的文化、语言、历史和人物都吸引她去亲眼看一看。
1985年,她终于梦想成真,可以去美国学习了。
离开中国之前,许多朋友和同事对她说:“如果可以,别把英语作为你的专业。美国人和我们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你永远理解不了他们。这是他们的文学,我们没有发言权。”
这些建议是有说服力的,但傅丹灵没有采纳。她说:“西方文学一直是带给我最多幸福和意义感的存在,我要去了解西方人是怎样通过文学作品来解读世界的,也想知道我的解读和他们有什么不同。”
傅丹灵很快申请到了罗德岛学院(Rhode Island College)英语文学的硕士项目。她想象自己坐在美国人中间,讨论他们的文学、世界和文化。
但现实给了她当头一棒。
每次上课前,她都会至少读两遍课程材料。但当讨论开始,她就感觉到,好像自己和同学看的不是一本书。她期待大家会解读文本、讨论作者意图、作者的思考方式。但大部分的讨论却从不涉及这些,大家会聚焦在一些抽象的符号、特定的画面或者宗教意味,会直接切入一些奇怪的论调,和现实世界似乎没有关联。
有一次,他们阅读一首诗,最后几句是描述波浪拍打在岸边岩石的情景。傅丹灵很喜欢诗歌里描述的景象,觉得它显示了一种自然的力量与美,象征着坚定和决心。但当课堂讨论开启,她震惊于大部分美国同学的解读:他们把坚硬的岩石被浪涛拍打形成的泡沫包围,视为具有性意义的画面。
傅丹灵说:“我们的世界差异太大了。没有人和我一样解读这首诗,我觉得自己被边缘化了,很无语。”
在这之前,她从来没觉得文学是个如此陌生、遥远、奇怪的世界。她开始迷失,每次离开教室,她觉得沮丧又挫败,甚至觉得自己根本不懂得阅读。
讨论《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时候,她的美国同学不是在讲费恩和吉姆之间可能存在的同性恋关系,就是在聊文本中使用的黑人习语。但傅丹灵想探究的是,马克·吐温怎样呈现费恩这个作为美国年轻人代表的人物、美国人通过费恩这个角色怎样看待马克·吐温、怎样通过人物角色看待他们自己。

这让她对阅读失去了兴趣,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听取朋友的意见。她努力维持这一切,通过Cliff’s Notes等“学习指南”模仿专业文学评论家的语调,尝试以“恰当”的方式去读写。最后,带着无助、迷失、沉默和疏离,她拿到了硕士毕业证书,那一刻她如释重负,没有丝毫的成就感。
不过,傅丹灵拒绝就这样终结旅程,做一个“失败者”,她决定继续读博士。也许是害怕再度经历这样被边缘化的四年,她把研究领域从英语转到了教育。
幸运的是,这次,来到新罕布什尔大学的她,像爱丽丝来到了仙境,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四年。
博士项目的第一节阅读课,她原本料想着又要听到一场关于形式主义或者解构主义的讨论,甚或是关于性意象或者象征主义的解读。教授出乎意料地在第一堂课上读了一个故事,让学生从自己的角度讲讲对故事的理解。大家都用平实的语言表达观点,不再像硕士时期动辄像专业论文一样作出回答。
傅丹灵开始觉得,自己不再是个外来者,不再是那个躲在角落里的人,而是和其他人一样的阅读者。
教授还让每个人讲述自己的故事,这让课堂上充满互动和开放式的讨论,也让习惯了“透明”的傅丹灵在最初有些不适应。但她并没有一个人待太久——老师和同学会不断用各种问题“戳”她,让她不断讲出自己的故事和想法。当她讲述自己在中国的故事,同学们都斜过身来仔细听。渐渐地,她语气中的不确定、羞涩变得坚定、充满激情。
教授鼓励她写下自己的故事。她不断地写下自己的经历、感受和想法,不仅有学术论文,还有诗歌和故事。其中一首诗这样写道:
一个没有名字的女人
我的外婆从未有过一个名字。
小时候,她叫做阿大。
结婚后,她成了苏夫人。
生了孩子,人们叫她张家妈妈。
我的外婆一直想要一个名字。
有一次,她晃着母亲的膝盖央求:
“妈妈,可以给我取个名字吗?”
她的母亲放下了手中的针线,转过头,沉沉叹了口气:
“孩子,我也想给你取个名字,但女孩不应该有名字。”
我的外婆一直很喜欢玫瑰,特别是红玫瑰。
一天晚上,她的妈妈在她耳边轻声说:
“红玫瑰,我可以叫你:我的小红玫。”
“红玫,啊,我喜欢这个名字。”我的外婆开心地叫起来,却有些遗憾。
她的妈妈在她睡觉的时候这样叫了她。
红玫瑰,这是我的外婆一直想要的名字,
但她只那样被叫过一次,在她睡觉的时候。
她活了71年,却没有一个名字。
在她的墓碑上,我们刻着:
张红玫
1880-1951
和博士项目里写作成就颇丰的同学相比,尽管傅丹灵的许多作品显得言语稚嫩,但这种书写让傅丹灵惊奇地发现,自己麻木的头脑苏醒了,不再是一直在试图伪装成他人的那个人。她找回了自己,仿佛又回到了那几年可以自由阅读、内心无比愉悦的时期。
她开始不断向同学提出自己关心的问题,也从未感受到一丝轻视,没有人会觉得她的问题太过细微或者幼稚。相反,他们总是耐心、热忱地回答和讨论,并对她的各种想法显示出极大的兴趣,认为这是来自东方的、具有不同视角的解读。
她说:“对于这一点,我原来是忽略甚至羞于提及的。我才发现,原来我的中国文化、学术训练和背景并不是一种障碍,反而是一种优势。”
令人欣慰的是,近几年来,美国大学中文学研究的领域已经不再局限于英国和美国文学,而是越来越多元化,其中也包括了中国文学。
从老挝的少年到中国城的移二代
这两段经历,先是将她边缘化,又解放了她。作为一名教育者,她很自然地想要帮助那些有过同样“羞耻感、挫败感、边缘感”的学生。潜意识中,她也想通过研究和自己有相似经历的人,和过去的那段经历和解,甚至以这种方式重来一遍。
1990年,她来到了新罕布什尔州一所叫做Riverside的中学,将研究视角落在了四个来自同一个老挝家庭的难民学生上。受到越战影响,当时这四名学生刚从泰国难民营来到美国两年多,处在14-19岁的年龄之间,性格各异,都遭受了语言差异和文化冲击,他们都希望自己能和本地的学生一样说英文、理解他们的想法。
但当时的学校教育没能帮他们和周围产生更多联系。尽管周围都是美国人,他们也一直浸润在英语环境中,花了很多时间学习词汇,却仍难以表达自己。他们口音浓重、词汇贫乏、对美国文化知之甚少,疏离于群体。

傅丹灵将他们的经历记录在了博士论文《My trouble is my English》(我的问题在于我的英语)中,这本书的名字就是其中一个学生的原话。
许多年后,傅丹灵仍和这个家庭保持联系。这四个学生有的离开了从小生活的城市,有的仍然留在家中,有的完成了硕士学位却仍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有的则在工厂工作。傅丹灵说,作为原先的“边缘人”,在30多年后,他们依然未能真正融入到主流社会——这和他们的工作有关,也和他们来美国时的“低起点”有关,即使是其中一个拿到硕士学位的学生,也没能把学业上的成就带到工作中。
30年前的案例,对于当下美国的移民群体也有同样的观照意义。傅丹灵在5年前去了一次纽约的中国城,发现那里和过去几十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她说:“他们这几个人的情况,和这么多年在中国城、西班牙裔区域的移民很像。你可以看到这种循环——父母生活在底层,孩子能起来的基本上也是凤毛麟角。”她观察到,大部分“移二代”会重复父母的命运,去餐馆打工,做建筑工人,许多家庭可能需要挣扎两三代人才能摆脱局面。
她认为,这些一代移民的孩子整体上受限于家庭环境,父母为了生计忙碌,没法投资教育,也很少在家里谈论启发孩子智识的话题,形成不了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
美国的公立教育正在经历一场危机
1997年到2007年,傅丹灵在纽约新移民较为集中的K-12公立学校,和当地老师一起进行文学教育工作,帮助学业表现较差的学生听说读写。
在她看来,如今公立学校中移民家庭的孩子并没有得到教育环境的改善——相比当年,时下纽约的公立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一种倒退。“纽约的教育变化很大,整个系统都在改变,老师们越来越多地为了考试而教学。这些孩子在家没有得到好的思维培养,在学校又为了考试而学习,很难说会有独立思考。”

傅丹灵表示,虽然这和国内为了“生存”而实施的“一考定终生”还有一定距离,但总的来说,应试教育不利于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的培育,孩子对世界的敏感性和好奇心容易丧失,和本应是“百年大计”的教育理念背道而驰。
究其原因,一方面,从大环境看,美国教育界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要通过考试成绩来和他国竞争,另一方面,不断更迭的政治环境也不利于教育理念的长期推广和实践。
在特朗普任期内,担任美国教育部长的贝茜·德沃斯作为一名“教育活动家”充满争议。她财力背景雄厚,长期资助各种教会学校,极力主张公立学校推广宗教教育,却对公共教育兴趣寥寥,她支持教育券(可使公立学校的学生有权利选择私立学校)和废除公立学校需要遵循的全国统一“教学大纲”(common core,被诟病为应试教育),她本人也曾就读于私立学校,还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了私立的基督教学校。
如今,尽管拜登重新提名了一位有过一线公立学校教学经验的教育部长,但傅丹灵认为,这些年来“翻来覆去”的政策已经已经对教育体系造成了非常大的打击。她说:“推广一个新教学方法要慢慢来,现在来一个就搞一套。”
她直呼,疫情中有那么多美国人罔顾巨大的死亡病例却宁愿相信新冠病毒是场骗局(misinformation),加之此前选举特朗普上台,这也印证了美国教育的失败。
过去的两年中,疫情把这些都放大了:公立学校要教很多内容,评定老师又都是按照学生成绩,老师们筋疲力尽,很难和学生建立良好的关系,学校更是急缺老师。根据K-12 Dive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48%的美国教师承认,他们在过去30天内曾考虑过辞职。在这其中,34%的人表示,他们正在考虑离开这个行业。
在傅丹灵研究的读写教育领域,现状也难说乐观。她说道,写作在美国的K-12教育中最不受重视,即使是一些最优秀的学生,在写文章的时候也觉得无比困难,“宁愿用代码来写”。
理论上看,美国的写作教育是为了让学生学会更好地和别人沟通、找到自己、探索思维。但在傅丹灵看来,这种理论和现实产生了脱节。“我虽然是这样培训老师的,但当老师到了学校,就会为了考试而教学生。”
拿佛罗里达的州立考试来说,四年级、八年级、十年级分别有一次考试,科目包括数学、阅读和写作。写作考试总分为5分,没有走题就可以拿到2分,其他的打分项包括文章组织结构、描述、拼写语法。但是,给学生打分的往往不是懂写作的老师。
傅丹灵说:“教写作需要花时间,老师要会改,会自己写,看书的时候自己能看出写作的技巧,用词、结构和文章的妙处都要能看出来,才能讲得好、引导学生。但是考试的时候,都是在看拼写、语法、结构,内在的逻辑、思考这些真正重要的东西看不到,这些没法用一二三来解决。”
移二代的身份认同并非无解
在北美华裔二代的成长过程中,文化身份的认同一直是个让人倍感挣扎的问题。
傅丹灵自己的孩子在青少年时期就经历过“希望自己不是中国人”的阶段,但后来就产生了转变,倾向于和华人在一起。她认为,这是一个慢慢认识的过程,对于青少年群体来说,他们普遍更希望自己“属于主流”。

“不过每个孩子不一样,有些孩子的社交需求特别多,也非常想和所谓的主流人群接触,可能这时候产生的痛苦就会多一点。”她说。
傅丹灵认为,在“移二代”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中,家庭、学校和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如果你自己的社区、种族在这里被轻视,孩子怎么会认同?如果是在一个大家都尊重华人的社会,谁会不愿意做华人?”
一些新移民要想让自己的孩子对“华人”这个身份产生认同感,首先自己就得关心社会并努力融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做一些社区服务。她认为,犹太人、印度人在“服务教育”上都做得很好,中国人也要努力走出门、进入社会、了解文化。她说:“中国人从小在领导力的培养方面欠缺,这也是华人较少做到高层的原因,如果父母能多关心社会,孩子就会感兴趣,想要去干预政治、影响社会。”
另一方面,家长自己也要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感到自豪,才能让孩子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傅丹灵说:“中国人的优秀要经常讲,孩子感觉到好了、了解了,自然就会喜欢。我的小孙女也是,我们不光给她看西方的王子和公主,也要看东方的故事,要让她对自己的美懂得欣赏,而这些都是点点滴滴的细节造就的。“
在所有的教育方法中,“谈论”是傅丹灵反复强调的。
“多和孩子谈谈,什么都可以谈,谈论社会上发生的各种新闻,谈思想、谈感情,只要孩子的好奇心被调动起来,就会去做很多事。”她在博士论文中写道,谈话可以帮助孩子们理解他们所阅读的东西,把外部的知识变成他们自己的——这对写作来说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可以帮助刺激孩子思考、组织想法、寻找合适的词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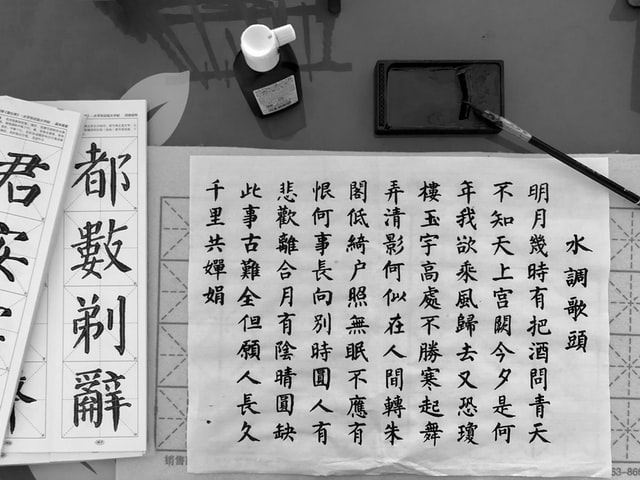
她认为,语言是沟通的工具,有些父母提出在家里尽量让孩子说中文,孩子的中文确实可能会好一些,但如果他们没有读过很多中文书,中文水平达不到自身的思考高度和深度,就还是应该顺应孩子的语言偏好。
“我比较相信translanguage(语言穿梭,指双语学习者可以使用不同的语言来和他人沟通),语言得跟着需求走,如果语言达不到表达的需求,实际上表达是被拉下来了,所以没有必要为了要保持一种语言而坚持。我们每个人其实也经常move back and forth(几种语言来回混杂)。”
傅丹灵认为,教育没有窍门,想要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自己就得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想让孩子做个好人,你自己就得做个好人、关心弱者。“父母从小就要示范,而不是比来比去、使劲找捷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