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的帕鲁尔·塞加尔发表书评,评论了文学学者马克·麦古尔的新书《万物皆缺:亚马逊时代的小说》,这本书通过分析亚马逊的Kindle自费出版计划(KDP)中的小说,研究了亚马逊改变小说出版业的多种形式,比如使小说被商品化,使作者为了争取读者而按照亚马逊的算法产出作品。然而,塞加尔认为,本书对于亚马逊的分析,反而让人发现了小说无法被商品化的本质。

这是绝望的时刻。作者坐在那里,蜷着身子干等着。太阳落山了。他把头埋在书桌上。情节,他必须想出一个情节。公众对故事如饥似渴,却对他精细的观察和微妙的人物描写毫无兴趣。他需要一个情节,他的出版商需要它,他的妻子也需要它,他们现在出生的孩子也需要。他缓慢地、艰难地挤出几段文字。
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1891年的小说《新寒士街》(New Grub Street),是对写作生活最无情的描写之一。故事的背景充斥着伦敦的写手、文人和文学界“最文艺的女性”,故事讲述了埃德温·里尔登(Edwin Reardons)在努力完成一本可能卖得出去的书时,那种紧张心情和财务崩溃的状态。他的朋友,圆滑而玩世不恭的贾斯帕·米尔文,认为他的努力完全没有必要。
米尔文认为,“现在的文学是一种交易”,是一种巧妙的谄媚行为。找出读者想要什么,然后提供给他们,还要有风格和效率。
拷问里尔登的不仅仅是作家惯有的魔鬼:低廉的字数报酬、自我怀疑、敌人的顺利升迁,还有主宰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界的三卷本规则。
所谓三卷本,是指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的作者)、乔治·艾略特(《米德尔马契》的作者)、本杰明·迪斯雷利(曾两次出任英国首相,曾撰写小说《西比尔》等)和安东尼·特罗洛普(《巴塞特郡纪事》等作品的作者)等人的许多作品的形式:通常是九百页的八开本,分为每卷三百页,印刷和装订得很好。
里尔登呻吟道,“这三卷书在我面前就像一个无尽的沙漠,不可能穿过它们。”
吉辛从他自己的日记中找到了这样的感叹;《新寒士街》本身就是一部三卷本,是吉辛的第八部作品,他用一切可用的技巧将它拉长,用尽全力地将它变得够长。“填充物交易”是当时特罗洛普对文学的称谓。
作为奢侈品,大多数读者无法直接购买它们,三卷本被英国图书发行巨头穆迪的精选图书馆(Mudie’s Select Library)所倡导。其创始人查尔斯·爱德华·穆迪(Charles Edward Mudie),经常大批量购买印刷品,因此可以要求出版商提供相应的折扣,而三卷本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的订户(每年至少支付一基尼标准费率的订户,基尼是贵族使用的货币,约等于1英磅5便士),一次只能借一册,每套三卷书就可以把书借给三倍的订户。
出版商们也同样喜欢这种形式,因为这使他们能够错开印刷成本。诱人的第一卷可以拉动对后续各卷的需求,并帮助支付这些费用。
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许多特色似乎都是为了填满那片“无尽的沙漠”,并吸引读者穿越它:三幕结构、拖沓的副线和庞大的人物阵容、令人震惊的悬念,以及通过口头禅或特别名字表明个性的人物,使他们在九百多页的篇幅中令人难忘。
狄更斯在《艰难时世》(The Hard Times)中给一个骗子起名为邦德比(Bounderby,英语中bounder被直译为行为不端的人,邦德比是本作品主要反派),就是一个无耻的例子。
小说中的自传和传记,比如《维莱特》、《简·爱》、《亚当·贝德》,都能很好地满足三卷本的要求;一个人生故事可以囊括任何必要的离题,并给它们带来一种叙事上的统一感。
三卷本一直都非常流行,直到19世纪末,穆迪对书籍过剩感到失望,并开始要求出版商提供单本的小说。随着用纸浆廉价印刷的大众化平装书的兴起,新的形式诞生了(低俗小说,或称Pulp fiction,名称来源于纸浆pulp),它们有自成一派的规定、引子和对读者的诱惑力。
但是,在小说的历史上,从杂志连载到互联网,小说风格一直是其发行模式的影子。在《万物皆缺:亚马逊时代的小说》(Everything and Less: The Novel in the Age of Amazon)中,文学学者马克·麦古尔(Mark McGurl)阐述了这个新的庞然大物如何改变了我们获得小说的方式,也改变了我们阅读和写作小说的方式,以及这是为什么。
他认为:“亚马逊的崛起是近期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新事物,它代表了将当代文学生活重塑为网络零售的附属品的尝试。”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正如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喜欢指出的那样,亚马逊以南美州的河流命名,它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河流,而且比接下来的五条最大河流的总和还要大。
亚马逊控制了几乎四分之三的新出版成人书籍的在线销售,以及2019年所有新书销售额的一半不到。与穆迪的公司不同,它也是一家出版商,有16个图书品牌。Amazon Crossing现在是美国最多产的文学翻译出版商,而亚马逊的另一个产业Audible是最大的有声读物发行商。
社交媒体网站Goodreads在2013年被亚马逊收购,拥有超过一亿的注册用户,而且,麦古尔猜测,它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丰富的文学生活遗迹库,仅次于世界上每台Kindle设备发回本部的大量细化数据。”
但是,麦古尔认为“对文学史最引人注目的干预”是亚马逊的另一个部门:Kindle自主出版(Kindle Direct Publishing或KDP);它允许作家绕过传统的看门人,免费自助出版他们的作品,而亚马逊则从中抽取很大一部分收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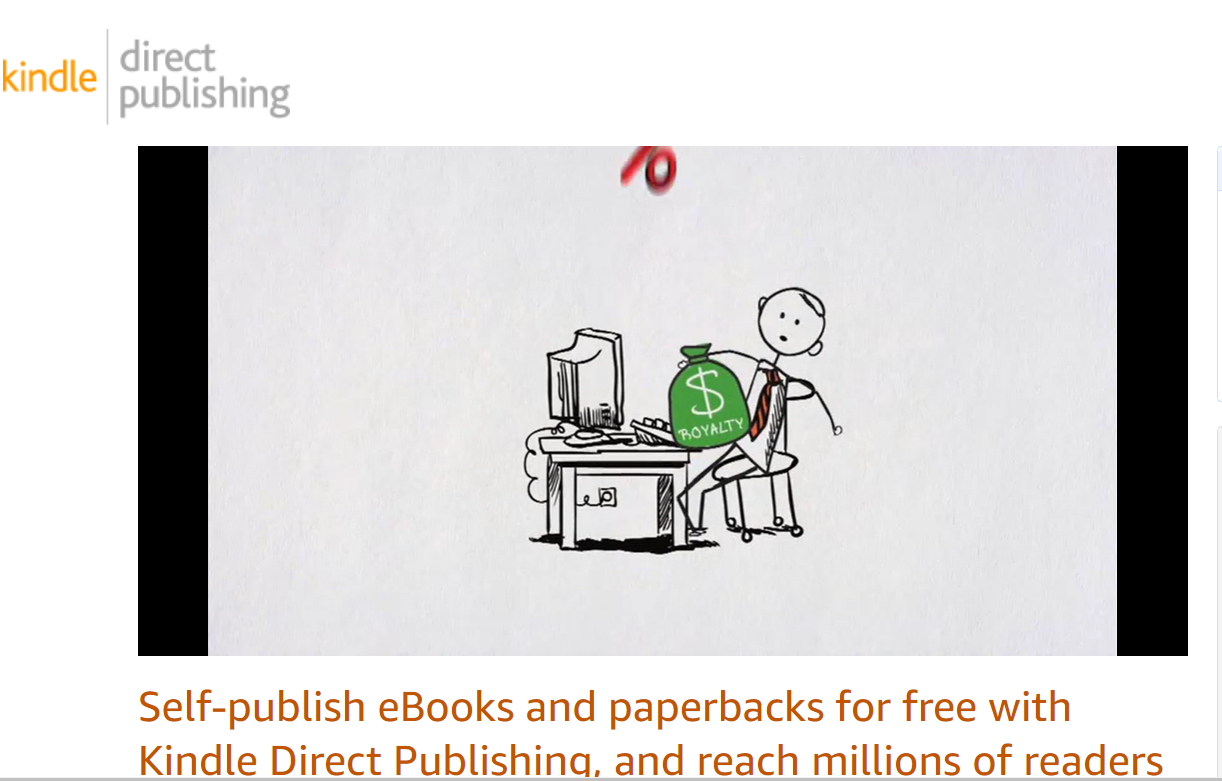
正如泰德 · 德克斯哈斯(Ted Striphas)和莉亚·普莱斯(Leah Price)等图书历史学家所写的那样,图书作为一种商品的概念并不新鲜;图书是第一个被赊销的物品。它们很早就开始使用条形码,允许以电子方式跟踪库存,这使它们很适合在线零售。
《万物皆缺》对这段历史一掠而过;麦古尔真正感兴趣的是描绘亚马逊的触角是如何插入读者与作家之间的关系的。这在KDP的案例中最为明显。此平台按被阅读的页数支付给作者,这强烈得激励了作者加入悬念,和尽快写出尽可能多的页数。
作者被要求不只是创作一本书或一套系列书,而更像是一条博文更新,即麦古尔所说的“一系列的系列书”。麦古尔说,为能充分利用KDP的推广算法,作者必须每三个月出版一本新小说。为了协助完成这项任务,自费出版的独立教程类书籍已经出现,包括雷切尔·亚伦的《从2000到1万:写得更快、更好、写出更多你喜欢的东西》(2K to 10K: Writing Faster, Writing Better, and Writing More of What You Love),它将帮助你在一两个星期内完成一部小说。
尽管这种方式更直接地关注于数量而不是质量,但KDP仍保留了某些奇异的标准。亚马逊的 “Kindle内容质量指南”中警告作者注意错别字、“格式问题”、“内容缺失”和 “令人失望的内容”,尤其是“不能提供愉快的阅读体验的内容”。
毫无疑问,文学上的失望总是违反了与读者之间的所谓“合同”,但在贝索斯的世界里,交易的条款已经变成了字面意义。
作者已死,服务供应者万岁。
反过来说,读者在当代市场上已经重生为消费者,其标志是满足特定欲望的精确性和可靠性。
麦古尔写道,“数字化的存在是一种液体化的存在,就像母亲的乳汁,流向需要它的地方。”
这就是比尔·盖茨所承诺的网络将做到的:提供“无摩擦的资本主义”。
采购产品的便利性能被转化为一种独特的美学吗?评论家罗布·霍宁称避免摩擦“本身就是一种内容,可读的书,可听的音乐,‘氛围,气氛等等”。
在亚马逊上,轻松消费的承诺甚至更加尖锐,在算法的鉴别下,书籍不仅仅是可读的;它们尤其是可以被你阅读的。
因此,麦古尔关注的是类型(genre)小说的爆炸,即今天出产的大部分小说。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书籍与亚马逊的服务精神交融的河口,它决心成为“地球上最以客户为中心的公司”。
当然,类型一直是图书营销的一个组织原则。机场售货亭的旋转架上闪亮的浮雕标签,向渴望罗伯特·路德鲁姆的惊悚小说或诺拉·罗伯茨的爱情故事的读者承诺了一种可靠的快乐。但亚马逊把这种定位带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浪漫主义读者可以把自己归类为“正派和健康”或“超自然”或“晚年生活”类的粉丝。而亚马逊在追踪了你的购买行为后,收到了信息,并会相应地为你提供建议。这些细分类型不仅实现了对质量的超具体承诺,也最终加强了公司对数量的承诺。除了在一个值得信赖的公式上进行变化,并无休止地重复以填满Kindle的无底洞图书馆之外,类型还能保证什么?
类型是特别能让自己的书在亚马逊上被“发现”的关键,在那里,书名被整齐地放入一个复杂的类别网格中。麦古尔非常平静地介绍了这些发展。他并不担心网格可能带来的压力,也不担心被推荐的书籍中可能会出现被剔除或同质化的情况。
他的核心假设是,亚马逊给读者提供他们想要的书,而他主要专注于辨别这些类型的功能,以及它们所解决的“需求”。
在研究浪漫小说时,他发现它们似乎激发了蔑视,部分原因是无节制的阅读和与之相关的糟糕阅读体验,麦古尔想知道为什么对重复性的渴望会获得嘲笑。他指出,毕竟许多乐趣都来自于重复,其中也许没有比阅读更重要的了,孩提时期,我们也曾吵着要反复听同一个故事。
在某种程度上,麦古尔自己也一直在关注同一个故事:美国小说的历史与支撑它的机构间的关系。
在2001年出版的《小说艺术》(The Novel Art)中,他研究了小说被提升为高级艺术的过程,因为现代主义作家在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小心翼翼地期望能将他们的作品与大众小说区分开来。在2009年的《程序时代》(The Program Era)中,他转向了创意写作部门对战后文学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对风格的影响。
他对美国特有的对阶级、享乐和大众文化的疑虑很敏感,这种疑虑围绕着阅读和教育而产生。在《万物皆缺》中,他带着对人类学的狂热乐趣,探索了长期以来被大多数主流学术和批评所忽视的类型和细分类型。

在这些学术荒地中,麦古尔发现了诱人的怪异、超现实的实验、怪异的政治乌托邦,有时甚至是甜蜜的。比如一个叫查克·丁格尔博士(Dr. Chuck Tingle)的行为艺术,他擅长撰写“挑逗性”(tinglers)同性恋色情,如《大脚海盗骚扰我的蛋》。
麦古尔还被佩内洛普·沃德(Penelope Ward)和维·基兰(Vi Keeland)的言情小说《傲慢的混蛋》(Cocky Bastard)迷住了。
他写道:“文学领域简直没有公正可言,这本小说远胜于《五十度灰》,更不用说白痴的《傲慢的室友》(Cocky Roomie)了,它有真正的幽默感,还由一只盲眼的小山羊充当配角。”
他还报告了KDP深处的“机会主义繁荣发展”,例如,《迷人的女性化之家》(The House of Enchanted Feminization)中的群交,代表了“即使不算是共产主义,也是向色情集群和社区的飞扑。”
他在每个地方都能找到对亚马逊的隐喻。他认为需求量最大的类型:僵尸小说,可能代表了亚马逊是如何看待它的客户的,它们成功塞满了贪得无厌的胃口。同时,成人婴儿尿布爱好者(ABDL)书籍可能是“亚马逊文学的典型类型”:一个典型的故事中:以妈咪克莱尔(Mommy Claire)的《诱惑、支配、尿布》为例,书中的男主角被女主角的母性关怀制服了。
这个男人的婴儿化体现了客户对亚马逊的依赖,亚马逊像一个称职的新生儿母亲一样,期望“将需求和满足之间的延迟降到最低”。“妈咪的写作中也隐含了一种惊悚的气氛,比如对惩罚和束缚的威胁,”它是“一个有益的提醒,即亚马逊对客户的迷恋最终是对其自身市场力量的投资。”
麦古尔的主张本身有一种诱人的怪异性,尽管它并不总是连贯的。
我发现自己在书中空白处严正地写道:“不是每次狂欢都是集体的。”
我也想知道他对“成功”KDP作家的定义。一项对自费出版的作家的调查发现,有一半人的年收入低于500美元。但是麦古尔并没有加入KDP作家们自己的声音(只除了收益丰厚的科幻作家休·豪伊(Hugh Howey),他是自费出版的非官方发言人)。他谈到了作者们的创新,但没有谈到他们的物质现实。今天的埃德温·里尔登们怎么样了?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从他们的写作中获得这么少的收入。
我们也没有听到那些对使用亚马逊这个平台感到矛盾的作家怎么说,或者那些感到被欺骗或被剥削的作家的想法。
可以肯定的是,麦古尔的目的是挑衅,而不是劝说。他不争论;他含沙射影,挑逗,触动,揉碎。他让自己在有条件的模式中变得舒适,他可以从中进行思想实验,然后把它们叙述成事实。他的武器库里充满了修饰语:“肯定是推测的”,“肯定是一种发散性想法”。
甚至他关于亚马逊如何改变文学文化方面的论点。也被随意地撤回了(这只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构建当代小说的故事,从而使一组特定的、以前未被充分审查过的现实得到缓解”),但接着在后一页之又被重新确认了。他对自己的辩护是内置的:“我们当中有谁又是完全一致的呢?”
而不一致的地方和小错误开始在脚下堆积起来。斯蒂芬·梅耶的《暮光之城》系列不是三部曲。玛吉·尼尔森的《阿戈纳人》(The Argonauts)是一本回忆录,而不是一本自传小说。“Bemused”(困惑)不是“amused”(感到好笑)的同义词,马克斯·韦伯(19世纪社会学家,西方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也很难指出新教资本家的酸性(acetic,笔误,大概指aesthetic,即美学)特征,不管他们有多晦涩。甚至麦古尔的开场论证也是建立在一个错误之上。
麦古尔引用了布拉德·斯通在2013年出版的关于亚马逊崛起的书《一网打尽》(The Everything Store),麦古尔在谈到贝索斯时写道:“如果我们把亚马逊的存在归功于他对石黑一雄的文学小说《长日将尽》(The Remains of the Day)的理解上,也并不是太离谱。”
《长日将尽》讲述了一个英国管家在意识到他在为他人服务时浪费了自己的生命,因此他声称贝索斯是在读了石黑的故事后才敢于离开他在一家投资公司的工作。但贝索斯实际上是在创办亚马逊一年后才读到《长日将尽》的。
他当时的妻子麦肯锡·贝佐斯,在亚马逊上对《一网打尽》留下了长达九百字的一星评论,她在评论中干脆地说出了自己的资历,“杰夫和我已经结婚20年了”,并纠正了这一记录。这个错误在斯通的书的后续印刷版中被修正了,但它在这里却仍然悬挂着,显示出麦格尔太急于将亚马逊自身也指认为一项 “文学事业”。
文学小说又如何能融入麦古尔对这种文学创作的描述?
他把它设想为另一种类型(其特点包括“可讨论的理解性问题”),并发现了其与大众市场浪漫小说的重叠。《五十度灰》中的阿尔法(alpha)亿万富翁的一个版本可以在阿黛尔·瓦尔德曼的《纳撒尼尔P的爱情事务》(The Love Affairs of Nathaniel P.)中潜伏的“贝塔(Beta)知识分子”中找到。(阿尔法和贝塔的称谓源于对狼群的研究,阿尔法是头狼,贝塔是狼群中的追随者)。
这类人对资本主义持适当的怀疑态度,精通女权主义,并且无休止地自我迷恋。麦古尔写道,这样的男人不想鞭打女人(《五十度灰》中的男主人公是性虐待爱好者), “只为了消磨时间”。这是麦古尔很轻易也很优秀地做出的俏皮观察;但他为什么不去看得更深呢?
他几乎没有谈到文学小说背后的特殊经济或它对出版集团的影响。他略过了亚马逊针对独立出版社的计划:瞪羚计划(Gazelle Project),这项计划以贝索斯的评论命名,即亚马逊“应该像猎豹追赶生病的瞪羚那样接近这些小出版社”。亚马逊的律师后来将瞪羚计划改名为(也许是个更令人不寒而栗的):小型出版社谈判计划(Small Publisher Negotiation Program)。

只有在考虑到亚马逊是如何预示着一个“过剩小说时代”时,文学小说家才会适当地进入麦格尔的叙事中。据报道,2018年,约有160万本书是自费出版的,它们都是在传统出版社发行的数万本书之外的。而作家又如何能在这股洪流中工作?
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窘境。《新寒士街》中的一位“最文艺的女性”。也对她自己身处的时代洪流感到沮丧,“当世界上的优秀文学作品已经多到任何一个凡人一生都无法应付的时候,她却在这里殚精竭虑地制造着印刷品,甚至已经没有人假装自己不是一件新鲜的商品。真是难以言喻的愚蠢!”
麦古尔认为有两种策略:与繁华接轨,走极致,写一部史诗,或者抵制它,在自传中寻找出路,将世界缩小到作家自身的身影。但当人们想起麦古尔在他的前一本书《程序时代》中也提出过类似主张时,这个论点就失去了一些光泽,他认为战后作家通过成为极繁主义者(他引用了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擅长批评美国社会)或极简主义者(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短篇小说作家)来回应艺术硕士项目中的阶层焦虑感。但当你想到大多数文学小说都不是这两者的时候,它就失去了更多说服力。
尽管如此,书籍的过剩可以解释许多当代小说中散发出来的某种耻辱的瘴气。作家索尔·贝罗(Saul Bellow)曾经说过,小说家们寻求对人性的定义,以证明其这门技艺的存在价值。然而,最近的小说则以羞辱为标志。在萨利·鲁尼(Sally Rooney)的《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Beautiful World, Where Are You)中,爱丽丝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作家,她认为她的书“在道德上和政治上毫无价值”。
还有琳达,一个在托尼·图拉希穆特(Tony Tulathimutte)的《私人公民》(Private Citizens)中挣扎的作家,她凄凉地想知道“什么样的作品可以存活下来?”或者安娜·莫肖瓦克斯的《埃莉诺,或,拒绝爱情的进步》(Eleanor, or, The Rejection of the Progress of Love)中的作家,即叙述者,她为她的手稿绞尽脑汁。
她告诉我们:“我列举了我书中的许多非原创特征它的段落性的结构,它平庸的故事情节,追踪晚期资本主义中的个人异化,等等。但真正让我感到尴尬的是,我根本想不出它的读者群。”
这种焦虑肯定会被作者和读者之间轻易建立的数字亲密关系所激起,读者很容易授予星星和评论,而这些就反映在销售点上。而且,正如吉辛与三卷本的斗争也成为了他的三卷本的主题那样,作者在数字亲密时代的焦虑本身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小说的一个独特主题。通过促进这种亲密关系,并按照同样的宣传手册操作,亚马逊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使所有的作家成为了KDP作家。更不用说它跟踪并挤压小出版商,削弱书店,并杀死竞争对手的做法了。

诚然,作家们一直在努力争取被关注,19世纪的作者居伊·德·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曾在塞纳河上放了一个热气球,为他的新短篇小说做广告。但今天的许多作家,无论是极繁的还是极简的还是中等的,都觉得有义务维持一个对话式的更新版面、“友好”的公报和通讯,用自嘲的方式直接对话,争取和培养读者。这是我们在劳伦·奥勒的《假账号》(Fake Accounts)中听到的自我意识音符,当她诙谐地将一个部分命名为“中间(无事发生)”时,她似乎是在管理读者的期望值。
而自我怀疑的想法则不断困扰着克莱尔·瓦伊·沃特金斯(Claire Vaye Watkins)的《我爱你,但我选择了黑暗》(I Love You but I’ve Chosen Darkness)中的叙述者(也是一个小说家)。因此当她意识到自己对作品的信念已经崩塌后,她在度假时偷跑去出席读书会。E.M.福斯特的《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的的引言中写道:“只要联系”,但越来越常见的是亚马逊向作家规定了这种联系的模式、方法和必要条件。
然而,《万物皆缺》在讲述一个故事的同时,似乎也在演绎另一个故事。在读完麦古尔将小说作为亚马逊时代的商品进行解剖的一切方式后,人们得出的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结论:即仍有那么多无法使小说被商品化的方式。
小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私人表达方式,而这可能才是这本书的真正结论。当麦古尔冒险进入所谓的文学生活的边缘领域时,他得到的惊讶和喜悦比他预期的要多。
这就是小说的本质;你必须在不完全知道里面有什么的情况下,跨过它的门槛。仅是拥有它并不构成占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