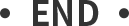引言
2020的开局,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注定要写上史书。
中国人民的“抗疫”战争,已经进行了两个月,虽然湖北武汉等主要疫区依然斗争艰苦,但是疫情扩散的势头终于出现了减缓的态势;
可与此同时,世界却不安宁了:
-
作为中国境外第一个中招倒下的日本,目前确诊人数超过千例,安倍首相宣布全国中小学停学,夏季奥运会前途未卜;
-
作为世界上除中国以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韩国现在确诊数目超过六千,单日增加病例超过中国;
-
意大利是欧洲首先沦陷的大国,目前确诊超过四千例,在过去的24小时内增加了25%;
-
伊朗的流年不利,自新年钟声敲响过后就显露无疑,目前确诊超过三千,三位内阁成员和议员大使这样的高层都被感染,仅官方颁布的死亡率就超过了10%,其毒力是世界最高的。
-
美国确诊数目达到两百,死亡16例,不明来源的病例在各地冒泡,疾控中心高层预言的社区扩散已成现实,在经济上,道琼斯和S&P一个星期跌幅都超过10%, 为继2008经济危机以来的最大股灾。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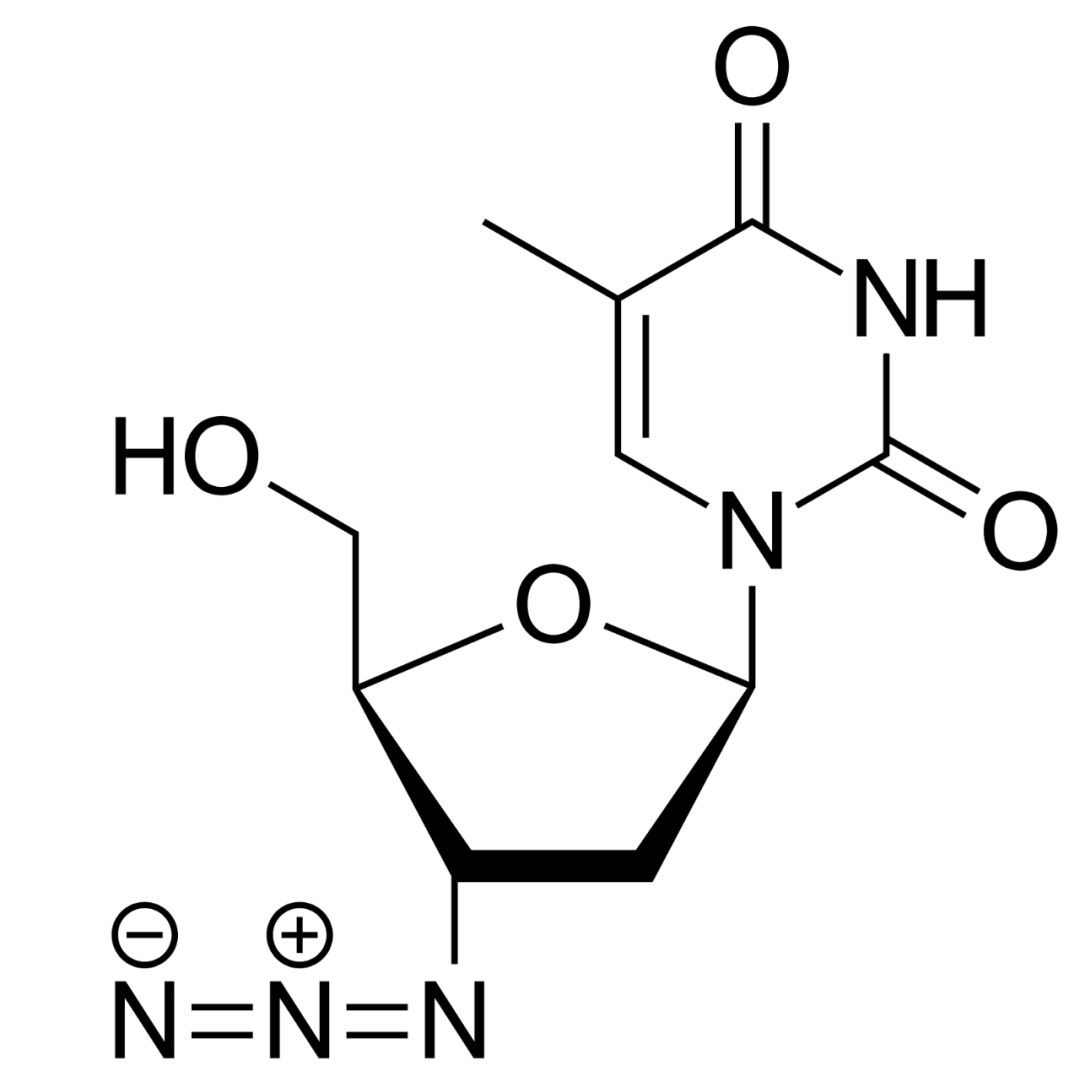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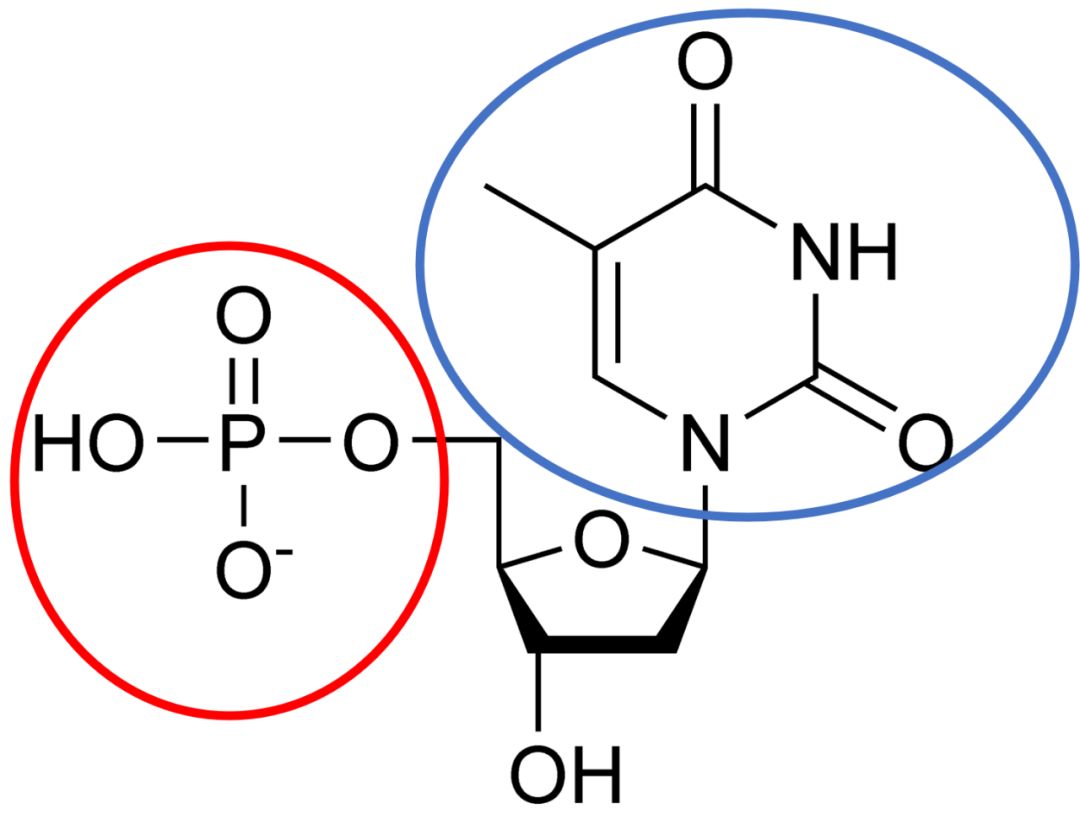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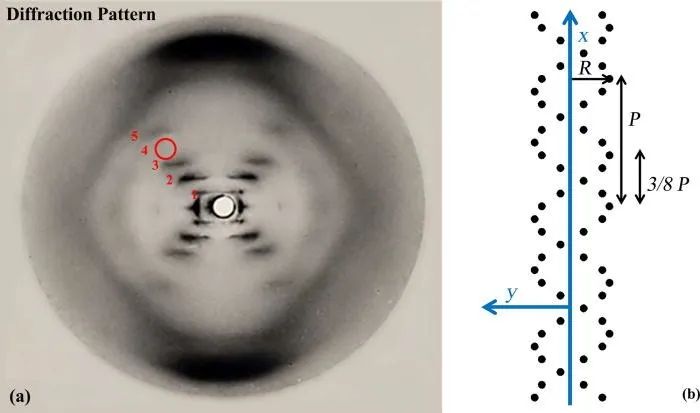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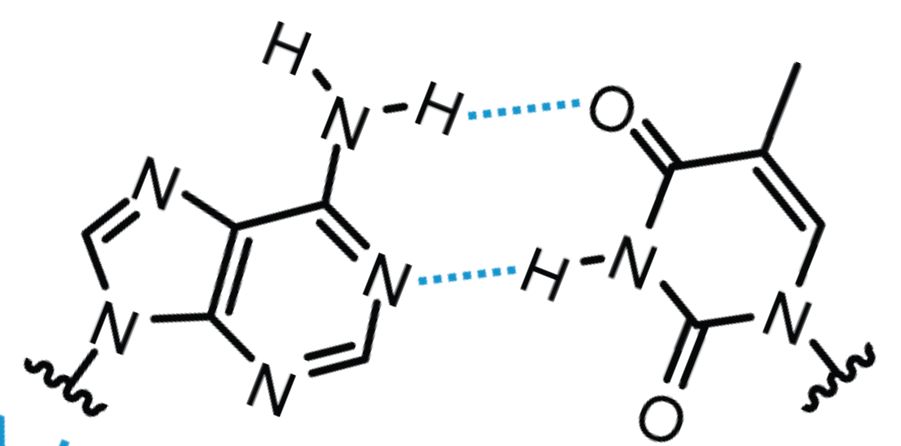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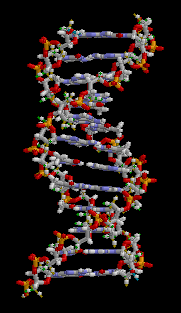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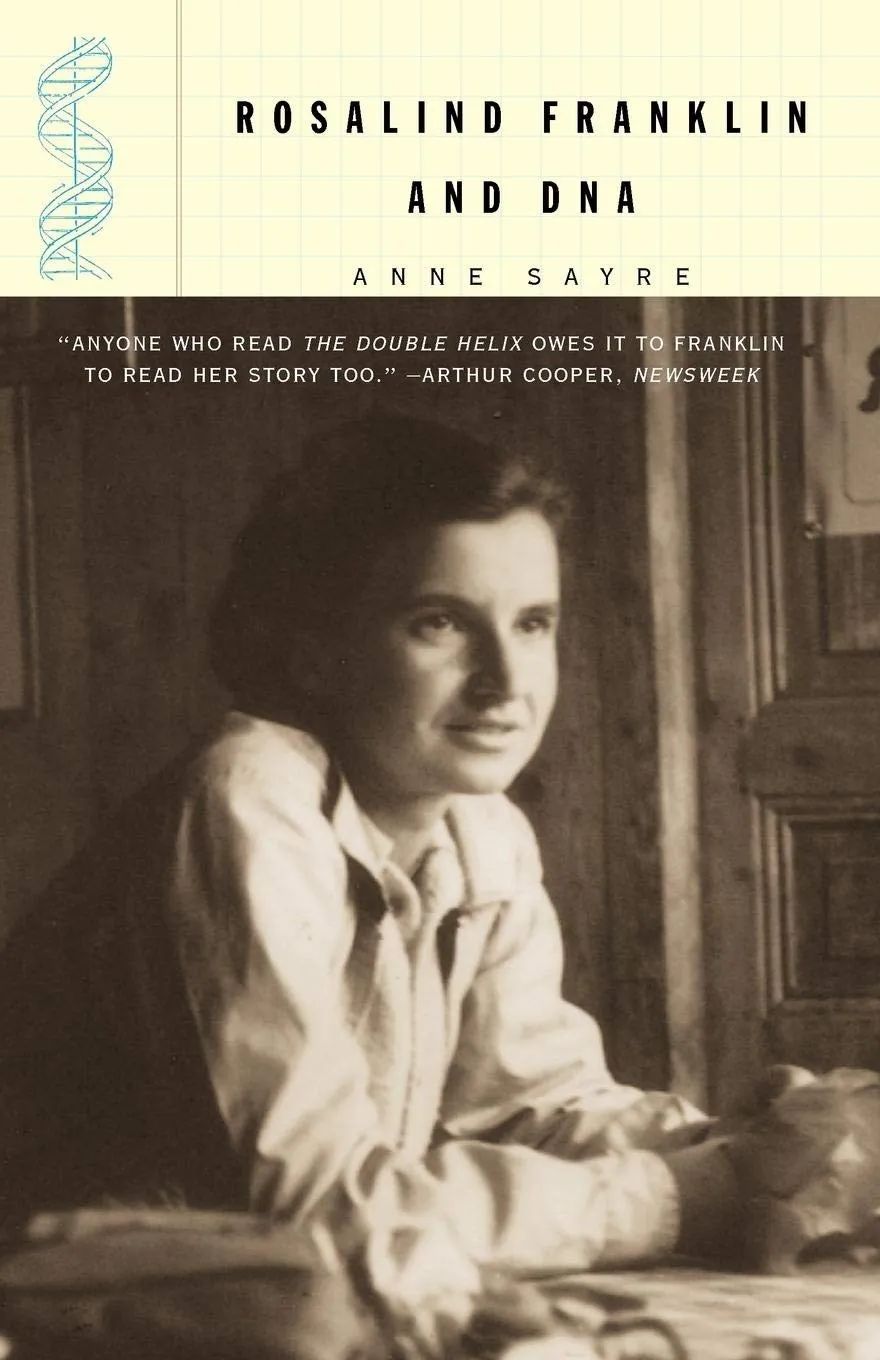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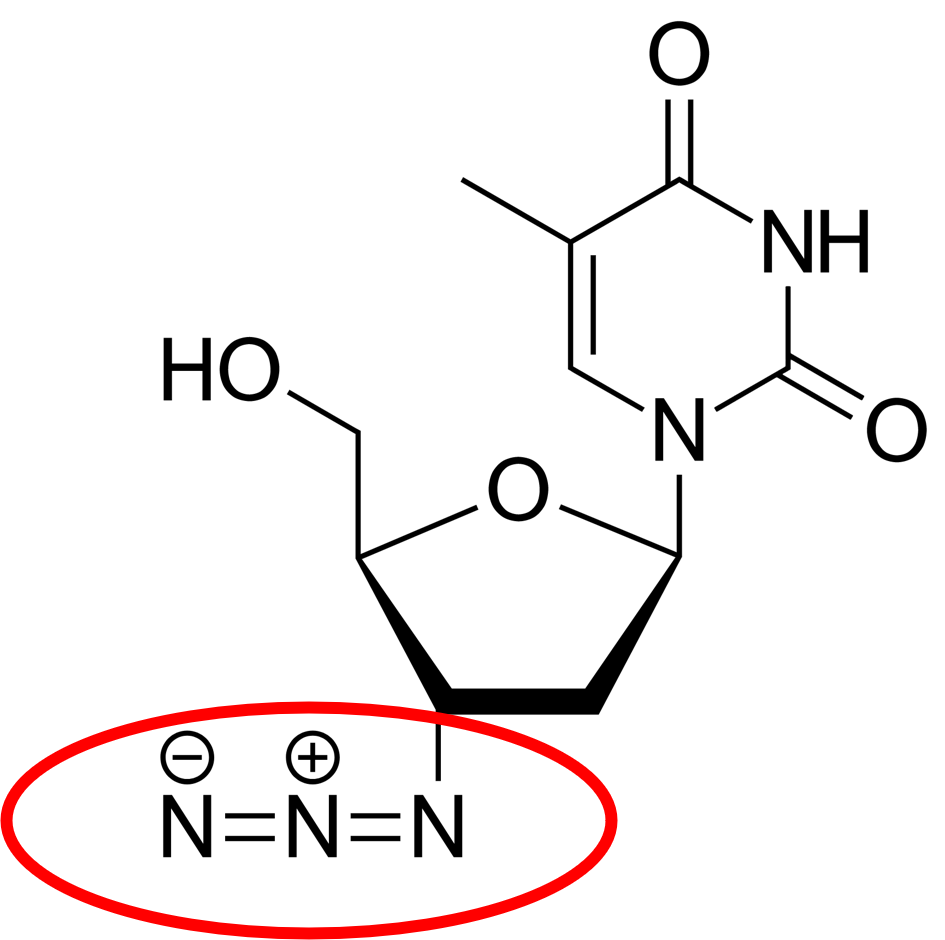
6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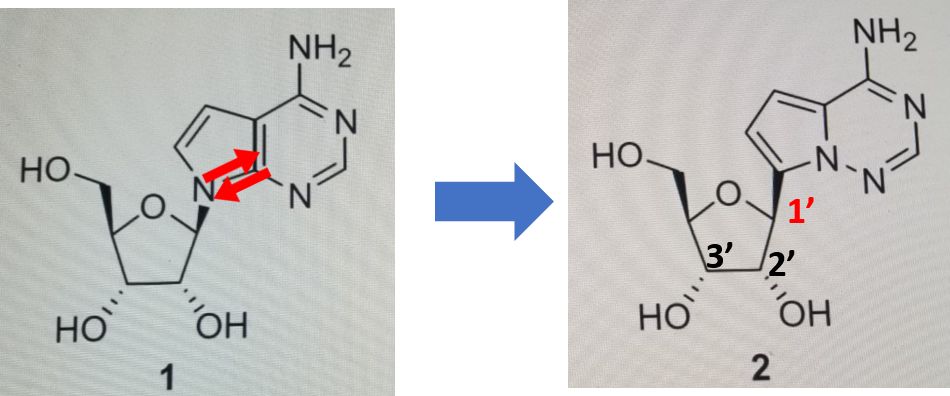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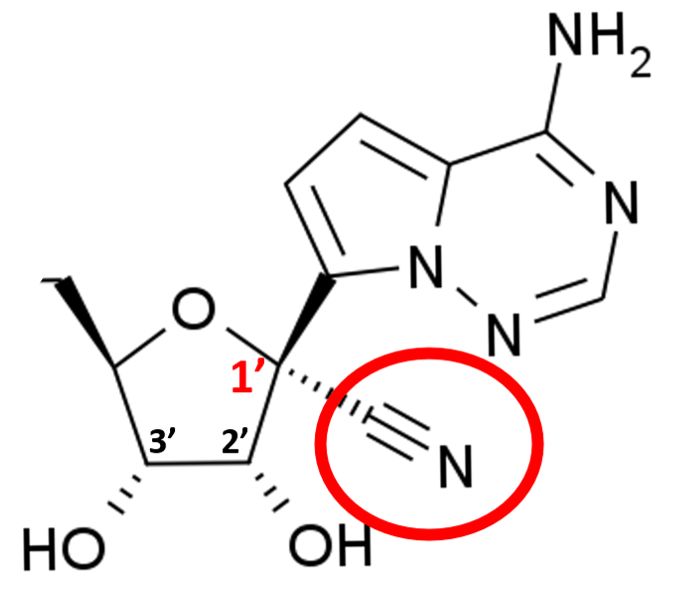

8
完
(图片都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