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外交学者沃尔特·R·米德日前与即将年满100周岁地基辛格共同午餐,讨论了领导力的本质,以及高品质政治家的匮乏使世界被民粹主义者和技术官僚所误导。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就在全世界的人们,对伟大领导力的需求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迫切的时刻,全球领导力的品质是否在下降?正如我在本月一次漫长的午餐中所了解到的那样:亨利·基辛格认为这正是事情的现状,他担心人类文明可能因此而受到威胁。
基辛格担忧是很自然的。他的第一本书《重建的世界》(初版于1957年)提出了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至今仍主导着他的思想。
基辛格认为:在任何时候,只有少数人了解一个可行的世界秩序的复杂结构;而只有为数更少的人具有创造、捍卫或改革微妙的国际框架所必须的领导天赋,使一定程度的和平成为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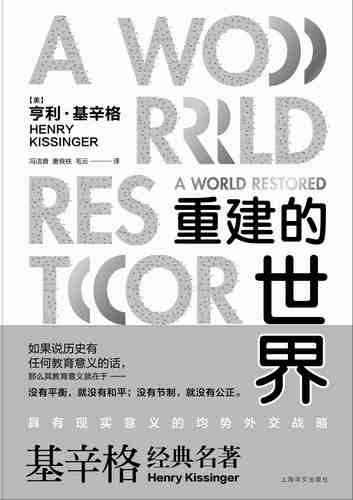
更糟糕的是:对于一个有效能的领导人来说,仅仅了解国际体系是不够的。基辛格认为:在任何一个国家,其公民希望看到的世界,和实际可能实现的世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世界不可能像中国舆论所希望的那样以中国为中心;不可能像许多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普遍民主化或清醒;不可能像许多穆斯林希望的那样信奉伊斯兰教;不可能像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希望的那样,围绕着发展问题作出反应;也不可能像英法两国国民希望的那样,对法国的宏伟壮观感到敬畏或对英国的道德领导力感到钦佩。
伟大的领导人,必须弥合本国舆论与外交中必然要发生的妥协之间的距离。他们必须清楚地看到这个世界,了解什么是可能的以及可持续的,他们必须能够说服同胞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经常令人失望的结果。
矛盾的是,在美国这样的大国里,这项任务往往更难,因为美国往往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它想要的很多东西。小国和弱国了解妥协的必要性;而大国和强国往往认为他们可以拥有一切。
伟大的领导力涉及到一种罕见的智力组合,即:博雅深厚的教育和对政治有着直觉的理解,这种理解很少有人能做到。基辛格的最新著作《领导力:世界战略六案研究》(Leadership: Six Studies in World Strategy)这本书挑选了六位在国内外取得巨大成就的领导人,分贝是德国的康拉德·阿登纳、法国的戴高乐、美国的理查德·尼克松、埃及的安瓦尔·萨达特、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新加坡的李光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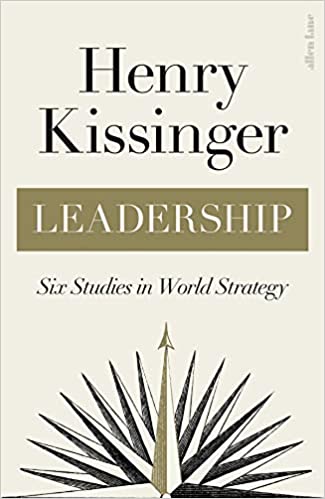
但这本书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正如基辛格在我们的午餐会上强调的那样:他担心使这些领导人能够出现所需要的特殊条件,可能正在消失。
他介绍的这六位领导人,都出生在当时社会精英阶层之外,他们是来自普通家庭的中产阶级子女。这种背景使他们有能力理解自己的同胞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他们被选入绩效主义(择优录取)的精英教育机构,接受纪律严明、要求严格的教育,这为他们参与在国家和国际政治生活的最高层有效运作做好了心理、智力和文化上的准备。
困扰基辛格的问题是:上述这种渠道是否正在断裂?今日的精英机构是否不再提供之前那种严谨和纪律,以及他所说的“深度识字率”(deep literacy)文化是否已经侵蚀到了社会,使之不再有必要的智慧来准备带来新一代人的领导力。
这不仅仅是关于“觉醒主义”的大学教授(注,这里说的是美国的woke文化浪潮,基辛格似乎站在保守派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使教育变得愚钝,或肤浅的左翼思想家将复杂和微妙的概念赶出了大学教育;这是关于经典学术的深度和严谨性,是否能经受住更多视觉文化以及当代媒体推动的更短暂注意力的挑战。
如今基辛格的人生度过了的第100个年头,他思考领导力问题的时间,比大多数今日美国人在世的时间都长。当他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公务生活时,老的WASP精英(即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缩写)仍然主导着美国的外交政策领域。
但像艾奇逊(Achesons,指时任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邦迪(Bundys,指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和艾尔索普(Alsops,指美国记者、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们这些为美国带来马歇尔计划和越南战争的老“婆罗门”们已经逐渐消失。尼克松、里根和老布什政府取得了重要的成功,但在21世纪,美国国家政策记录却不那么鼓舞人心。
基辛格警告说:今天,世界秩序的问题越来越难解决。大国竞争加剧,中国是一个比苏联更复杂的挑战,随着全球冲突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国际信任也在减少。他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智慧,但并不那么容易找到。
这一点很难说他说的不对。今天美国国内的辩论,无论是国内政策还是外交政策,往往是沉浸在传统团体思维中的技术官僚,与手持肤浅口号的民粹主义鼓吹者之间的毫无意义的竞争。亨利·基辛格认为,我们需要做得更好。
我担心基辛格是对的,我希望《领导力》这本书能得到广泛的阅读和关注。


